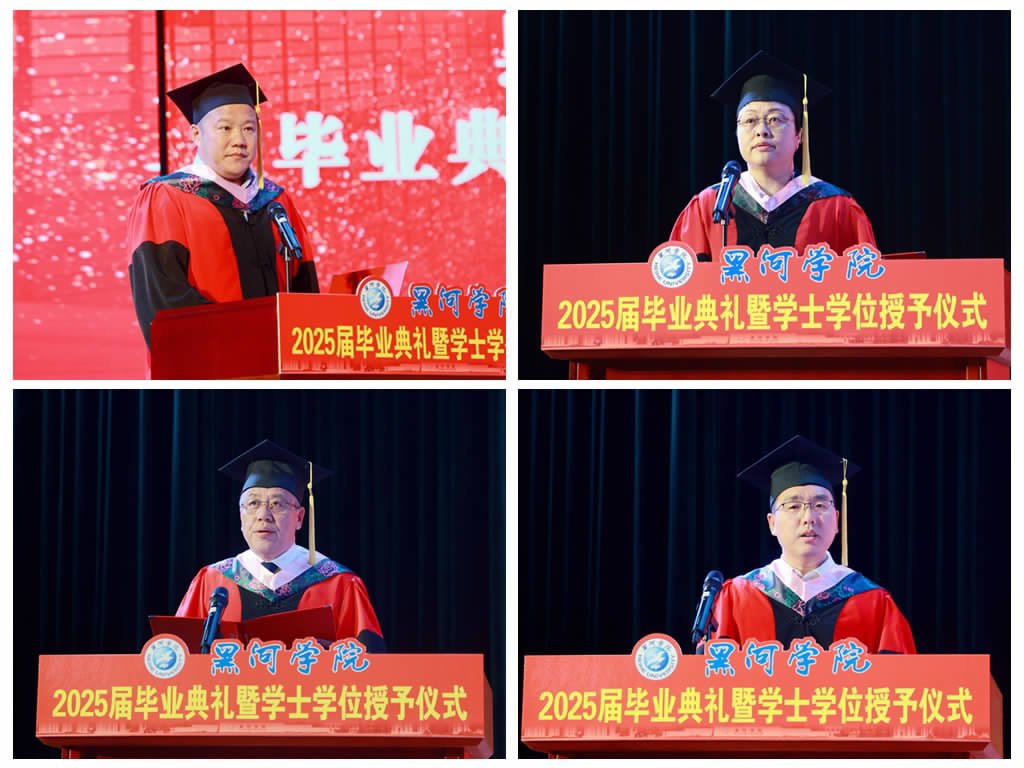记得当年上学时,遇到过许多老教师,得到过他们非常好的教诲。也许正是因为老教师身上那些传统的有厚度的东西,才让我格外留恋。
先说说我初中时遇到的地理老师。他长眉大眼,清瘦严肃,微驼的腰,嘴角很少能往上翘。和那时许多老教师一样,除了节假日,他都住在学校里。简朴微昏的宿舍兼办公室里,到处是地理方面的书籍,各式地图和地理的器材。干净利落的床铺上随意摆着几本书和我们几个班的作业。那里有他刚劲有力又不无耐心的批改内容。他一有空就泡在各个教室里,背着手来来回回地走,鹰一样犀利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课桌、每一页作业。忽然停住了,身后长长的木棒拿出来,指住一页地图:“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哪里?属于哪个国家?连接着哪些海域,有什么重要意义?”被指住的学生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立即答出这些问题。否则,他说过大棒立即打到身上。不记得我们有没有人被打。但即使当时最不好学的学生现在说起来,都说到全国旅游不用翻地图。
记得还有一位代数教师,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脑袋,戴一副大框的棕色眼镜,遮住了一只有问题的眼。他太幽默了,时不时记出几个俚语典故,惹得我们哄堂大笑,大笑之余,也把他讲过的公式记了个牢靠。平常他一支接一支抽烟,熏到脸也发了青。走路也慢,像在踱步。但只要一上讲台,立刻像上足发条的陀螺一样,又是动作又是表情,又是高音又是板书,红红绿绿一黑板的公式写完后,枯燥无味的代数课上出了别样的味道。他还有最拿手的绝技是背诵 《三国演义》全书,背下了一本的《新华字典》,偶尔还会表演一段。让我们知道,语文数学原本就不该分开。
这样的老教师,还有我高中时的英语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直到毕业20年后碰见他时,他还能叫出我的名字,如数家珍地说出许多学生当年的典故。其中就有我因晚自习躲在厕所看课外书被他抓住的事情。他还笑着问我是否对当时他毫不留情的一番批评耿耿于怀。当年最难堪的是他问我一道古文题,我答不上来,他对着呆若木鸡的我奚落一通:“你不是语文考第一吗?连英语老师的问题都答不了,还敢说第一吗?”我在无地自容的同时暗下决心,一定要做语文专家,一定博闻强记,绝不松懈,以免落下更大的笑话。后来果然取得了很大进步。
还有另两位老教师。一位是高中补习时的班主任。补习班七八十个人,这个语文好,那个英语差,情况各不相同。班主任就天天在班里调查,非要按每一个人的情况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他还是位代数“考试专家”,他把总结的一大本代数应试技巧倾囊相授后,我原来只能考四十九分的数学涨到了七十九分。但他还不满意,又很坦诚地在全班同学中推广我的英语学习法。另一位是女英语教师。她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常自嘲可以嫁给我们了。有一次,我因病误了一周课,她就在每天放学后把我叫到办公室补课,每次半个多小时,分文不取。
除了这些老教师外,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当年雁北师院的、儒雅得有些迂腐的毕致仁先生、睚眦必究的江阴褆先生。两人是夫妇,在他们夫妇的教诲下,我对语文的理解感悟远胜从前。毕老师的女儿曾因我写过怀念毕志仁先生的一篇文章而十分感动。这也算是我对师恩的一种“回报”吧。遗憾的是我至今没有再见到两位先生,没有机会再次向他们表达我最崇高的敬意。
真正认真负责的老教师,正是中华传统美德、中华精粹文化的维护者与传播者。真诚地希望,这样的老都师能遍布我们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年级、所有的班级。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生活在这样的老教师的呵护与指导下,夫复何求。(作者系文学院1996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