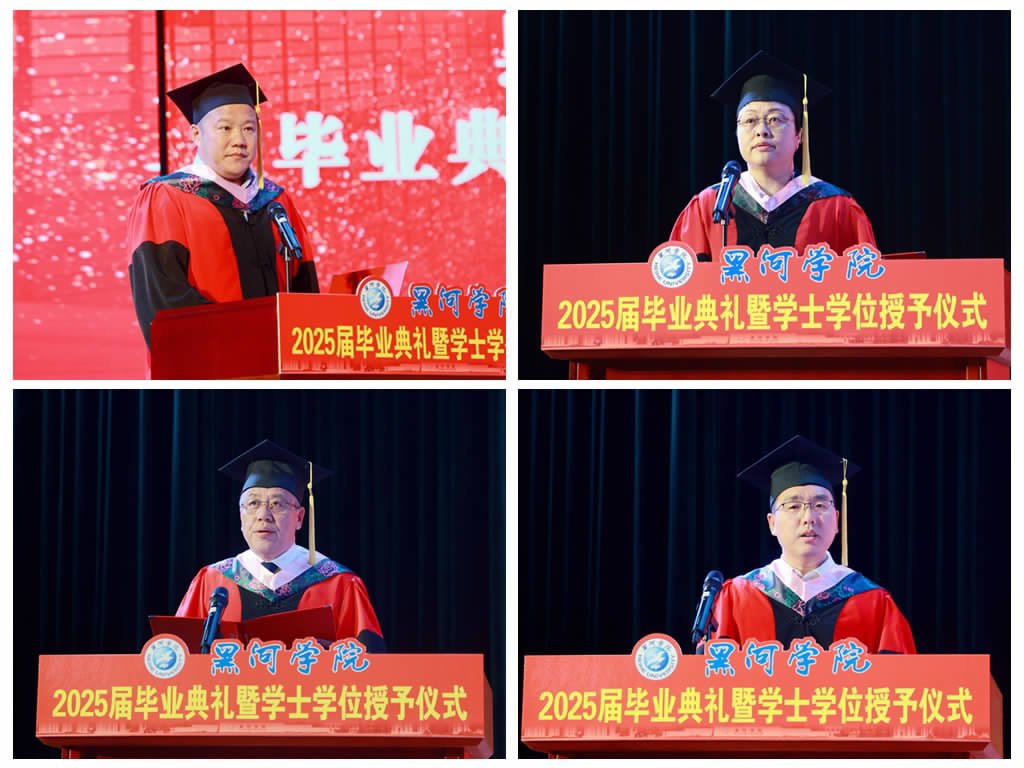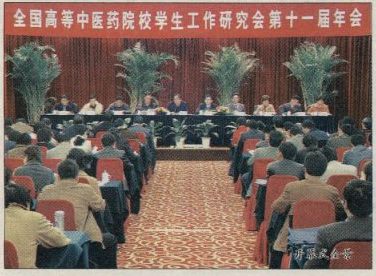曲园二张:张元勋先生和张秉禾先生
与 “园”有关的词,有 “校园” “家园” “田园” “园林”等词,以园字立名,而又能体现诸词内涵的,当有 “曲园”一词。
我从曲园毕业,至今二十余载。这当中尘海翻伏,教务繁忙,没有闲暇能重沐母校惠泽,只能从校友录中零星了解母校的一些人事,还有母校沧桑变化的历史。残缺之为美,距离之为美,说不清有多少美学意义,于我而言,更激起了我对母校的怀恋。怀恋却不能重新徜徉于曲园中,对曲园也就更加魂牵梦萦。这种情感一经母校师友烙印,便刻骨铭心,须臾难忘也。曲园二张,即其人也。
一张,乃教授古典文学的张元勋先生。张先生乃中文系四大怪之一。说起中文系四大怪,我不甚明了其由来,只是粗略听说这四个人 “恃才傲物”,系里开会时四怪就成了主角,会场相逢,一经触碰,便口锋相争,时事世态,古今趣闻,名流雅事,鄙俚街语,学问世理,无一不入辩,加之四人口才好,谈锋健,又当仁不让,俨然成会议主角,真正的主持人往往成了旁观者,与会者成听众而甘乐焉。
四怪究竟怎样,我不甚了了。不过元勋师的博识与健谈在我等入校不久就领教了。
大概是学校地处圣人故里之故,系里在入校不久便组织八九新生游 “三孔”,元勋师当导游。时值秋天,曲阜的秋天里似乎总弥漫着灰尘,可能这就是带着风尘味的历史感吧!我们这些从各地会于一处的学生还没洗尽旅尘,身上仿佛还散发着火车或汽车的味道,人地生疏,对于一切还很迷茫。
那个秋天的下午,阳光不是很亮,秋风还没萧瑟,秋草纷披,路旁的树也初显枯黄之意。我们一百四十多号人,杂乱地挤在孔子故里的某个角落里,纷然不知所往。这时候,元勋师在一旁微笑着看着我们。当然一开始并不知道是张师。时至今日,我分明记得那淡如秋阳的笑容和那张略显沧桑的圆如朝日的脸。这样的场景在时隔十几年之后越发清晰。有时时间不会冲淡什么,反而随着它的逝去,一些浮沫和杂滓也会随之被撇去,留下的是纯真的、值得怀恋的人和事。
从来没有想到历史与我们这样贴近,在呼吸之间,在视听之间,到处是历史的遗存,一段残损的城墙,一块风雨剥蚀的古碑,一根古木,甚至一堆乱石,都氤氲着民族源头的烟云:万仞宫墙、金声玉振坊、先师手植桧、大成殿……在别的地方,历史是发黄的纸页上的竖版字,而在这儿,历史是可碰可触的实物;在别的地方,老师讲历史等于纸上谈兵,而我们的元勋师则用他那渊博的学识和健谈的口才把我们拉进了具有历史真切氛围的磁场中。
“不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原定一下午游三孔 (孔庙、孔府、孔林),可是从中午到傍晚,我们竟没逛完孔庙。暮云四合之际,才走到大成殿。也难怪,有这么丰厚的历史积存,有渊博如张元勋师的硕谈,我们有幸躬逢如此盛事,我们甘愿浴历史的长河,我们希望那样的下午能重现,能重温先生的雄深雅健。
“不学 《诗》,无以立;不学诗,无以言。”在庭训之处,张师言孔子如是说。其时,我等正是叨陪鲤对之童耳。我们那些学子啊,风华正茂,意兴遄飞,似乎功名事业,立马可待,见绿柳而兴诗,见红棉而怡情。 “少年不识愁滋味” “为赋新词强说愁”,不识愁的少年,焉知世道艰难?
时间长了,对元勋师的事也了解渐多。他学识渊博,口才好,谈锋健,早年被打为右派,境遇颇为坎坷。我现在想,他的知识来源于北大的学术圣地和良好的师承,他的健谈来源于他的才华,他的坎坷源于二十多年不便言说的境遇。
张师蒙冤二十年,然志节不改,旷达如许。他曾言及自己,在松花江边劳改,看一江春水滚滚东流,其时朝阳东升,云气霭然,先生两手扶腰,目送流水如归鸿远去,宠辱偕忘。其言语不能实录,但上课之情形与先生言及之文人风范竟是历历在目。
最难忘的是先生说到忘情处,竟然蹲到讲桌下作朝日初升状,在中文学子的瞩目之下,一轮苍颜从课桌之际冉冉升起。华发如雪,圆脸如日,冉冉升起者,先生师道之心耳。此瞬间一经定格,是永生难忘的。
先生之举实乃不言之教。他于苍颜华发的 “冉冉”中让我们这些即将为人师的师范生,让我这个如今仍为人师的人明白一个老师最根本的师心――亲切平易,如坐春风,如沐朝日。
也就是在元勋师给我们讲授先秦文学史期间,我认识了另一张———张秉禾先生。其实跟张秉禾先生的认识纯属偶然。在写作课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老头来旁听课,或者在别的系别的课上也能看到其人。一开始我们很奇怪,在我们那群还很青涩的青年男女中,出现这么一个满脸沧桑、头发半秃的人还是很显眼的,也明显地不协调,故私下呼之 “张老头”。
“老张头”早年参加革命,当过新四军,这可在课堂上得到印证。有一次,逻辑老师给我们布置作业,我们在底下作为难状,老师站在讲台上也作为难状,彼此心照不宣。我们都知道,张老头却不明就里,看到我们作为难状,以为我们真的不会,便站起身,慷慨地做一番演讲,大意是像他这么大年纪,尚且有信心学好,何况我们年轻。说着张老头竟挥起手,唱起了歌,声音苍老而模糊,细听进去,能听出诸如“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的词句。以此可见他确实当过新四军,而且他唱时四顾空阔的投入,俨然重回当年铁血岁月。看来军歌中昂扬激奋的旋律激励着他,他也把学场当成了战场。这与当时中文系的课堂和学子的心态是很不协调的。我们都笑了,说他受了刺激。
几经辗转,他来到曲师,年近半百,娶曲阜当地的一位女子为妻。从日常生活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这诸多差异竟促合成这段奇特的姻缘,丈夫搞学术,妻子做清洁工,俩人相伴相守,守护着时光深处最琐碎的生活细节。这在当时的我看来非同寻常,非有大经历、大包容的人不能如此。
张老有着自己别样的追求。他把自己的住处命名为 “西南园”,屋里挂上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字,屋外种着几竿修竹或几棵翠绿的花生或长蔓的地瓜。看来他也可能有冥然兀坐,偃仰啸歌的雅兴。还有一张相片,图示某年他种的瓜收获了,他竟专门抱着瓜在萃华园的樱花树下 “立此存照”,那得意的神情,使他饱经沧桑的脸上竟平添了几分孩子似的憨痴。
其实不止是张老头怪,在曲园中还有很多可以称怪人的。比如教外国文学的仝老教授,在饭后闲行的甬路上或在课间闲聊的走廊上遇见他,我们可以不鞠躬或呼以“老师好”,而加食指朝他一指,这一指老先生竟也会哈哈大笑,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反而其乐融融。指毕,言笑而过,路遇之礼可算是完成。
教育家梅贻琦教授曾提出: “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彼时曲园,楼不甚高,尚有平房如西联一、西联二者,门前大树葱茏,自春及秋,荫庇一方学子之乐土。砖甬泥地,清雨微霜,土气沛然,自地面直入学子心间。园名萃华,曲水亭榭,行者有通幽之叹,也可以留连其间,学圣人曲肱而卧,视富贵如浮云。时节所至,绿树幽竹,各色野花,随时开放。有吐纳古今的图书馆,嗜古者有线装的古书,伴其清茶一杯;喜今者可以马列毛邓,各寻其圣。学不甚严,可以在教室集体听课,可以在自修室研读,也可以黑甜一觉,不知所之。傍晚时分,夕阳西下,青野之上,绿水之畔,禾稼声影,惠风扑面,有教授学子漫步其间,可以冥想学问,也可散逸胸怀。于今想来,那真是曲园最好的光景。
我的校友王开岭在 《激动的舌头》中这样说: “它 (曲师)自有令我怀念和尊敬的地方:学风健正、敦厚;一座藏量丰富的老图书馆;伙食价廉物美;整座校址被庄稼结实地包围,夜晚空气爽魂,飘弋着野菜的懵懂与沁凉,最适于散步遐想———你会为随时打破自然与文明的界线而心情舒畅。”他是以近乎哲人的眼光看待曲园的,说出了曲园赋予学子们的共同感受。
尤其感怀的是,曲园不但是我们的母校,更容纳了像二张这样怪倔至极的人,给像他们一样经历坎坷的大师能有最后一方相对安宁的空间来经营他们的学术天地,让他们的芳香的思想随时间而氤氲久远。
曲园因为自己的慷慨仁慈、宽厚质朴,成就了两位姓张的学师。
如果说曲园二张的题目有什么兴寓之意的话,可能就在此吧。
(王成强:中文系八九级校友,现于威海二中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