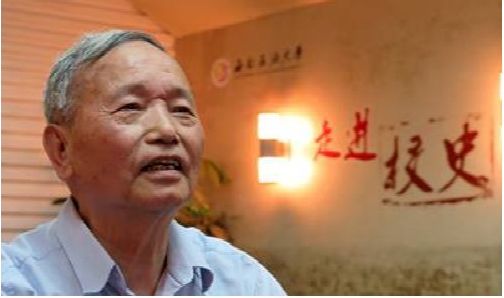
我是被“抢”来的
学校成立的时候,我刚在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并留校作助教,已经开始上班了。四川石油学院一成立,王良初和葛家礼作为四川石油学院的代表在北京石油学院要人,因为他们两个是北京石油学院的,对教师很熟悉。另外,同时还有西安石油学院的代表在要人。我先是被西安石油学院抢走了,当时是星期六晚上,他们没找到我,学校放电影,还在放电影的中间广播通知过我,可是那天我没去看电影。第二天吃饭的时候,我们教研室的老师说:“西安石油学院的都走了,你怎么还没有走啊?”,我说“我不知道啊”,他们说“昨晚放电影时通知你啦”,我说“我没有去看电影”。就那么一天的时间,葛院长他们又把我抢到了。结果西安石油学院抢了三个采油的,四川石油学院抢到了六七个。办了手续我们就到四川石油学院了。
当时四川交通十分不方便,我们走了一个多星期才到南充。因为快到西安时,遇上宝成路塌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抢通,于是我们下车了,在西安石油学院住了两晚,路修通之后我们才赶到了成都。
当时成都到南充没有直达汽车,必须先坐火车到石桥,途中还要经过两次摆渡,又坐了整整一天汽车才到南充。到南充后打听到学校地址在飞机坝,我们到了飞机坝时,学生都已经到了,教师职工很少,只有几十个。
组织学生参加井队劳动
当时晚上没有电灯,用墨水瓶装学校发的煤油,用鞋带做灯芯来照明。那个时候,不光是没有灯,下雨的时候根本出不了门。一下雨,那个稀泥很深,四川的同学有相当一部分打光脚,踩着稀泥也不怕;我们刚从北方过来,穿鞋习惯了,所以没办法,我到四川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双半高筒的雨靴,不然出不了门。后来,咱们地质系的学生看到只要一出门吃饭就是一身泥,那咋行呢!所以地质系的学生就用煤渣铺了一条到食堂的路,还很隆重地命名为“尖兵路”,因为搞地质的是尖兵嘛。
当时在飞机坝组织了两种劳动,一种是农业劳动,老师和学生一起到曲水乡挖红苕;还有就是组织学生到井队和石油现场参加劳动。当时四川油气勘探规模已经很大了,我们一部分人到龙女寺,一部分人到营山。我和北京石油学院调来的一个老师带领学生到东观参加输油管道建设。
当时学校从东北的炼油厂调了一批相当有经验的技术工人,有冯玉亭、常在乾等,这些工人师傅的技术水平过关,是骨干。去东观的学生都是跟金工老师住在一起,租农民的房子,稻草一铺,一间房子睡好多人。我们先挖管沟,管沟挖好后,就用木头做个支架把两个管子吊好,水平对接上了再焊接,冯玉亭他们就指导学生焊接管线,金工老师给学生讲课,讲电焊、气焊,为什么电焊、为什么气焊,有什么要求,就现场讲一点,没什么讲稿。
十二月份天气比较冷了,水田里面照样干,劳动强度相当大,学生干得很苦的,比如说车子把管道运到公路边后,要把管子抬到管沟那儿去,那都是学生把管沟挖好,一个接一个
地抬进去铺好,干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样子。
建校修路地质系排第一
到了 1959 年,学校开始建校了,搬到金鱼岭后条件比之前稍好一点,因为这里有电灯了,其他还是差不多。金鱼岭是住集体营房,五六个单身老师住一间,也是教研室开展教研活动的地方。那时老师已经比较多了,开始分教研室,成立了地质系,包括钻井、地质、采油;机械系包括矿场机械和石油机械;炼制系包括人造石油和炼油,总共成立了四个系,分别都是由老干部来担任书记。比如,地质系是付义,机械系是杨长生,炼制系是谷长富。
搬过来以后,就开始边建校边劳动,老师和学生都要参加。当时没有道路,只有一条通往砖瓦厂的烂路,其他地方都是农田,要建校就先要修从砖瓦厂到学校的这条路,建筑材料才能运进来。我们地质系的老师是在露天会场,用十字镐挖鹅卵石,再用箩筐把鹅卵石担到老校门口垒起。每天干完后基建处都要来量,哪个系今天交了多少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地质系是干得最好的,人均一天有 1.1到 1.2 方。当时干得热火朝天。为了尽快把路修通,我们还建议更改了路线,缩短了路程。
虽然学校当时条件艰苦,条件差,但是来到学校我从没有后悔过。我们那个时候教育都是这样,国家的需要,党的需要,就是应该自己去干的事儿。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一名党员,我不能挑三拣四。
千方百计开始上课
几个月后的一天,教务处处长李直找到我,说“黄逸仁同志,咱们现在对教学的准备工作要考虑得远一点,做一些必要的准备。经过党委研究,让你去成都工学院进修《水力学》,任务就是去听课、备课、试讲,给你半年时间准备这门课程的开课。”这样,我就没再参加学校建设,而是去进修了。
在成都工学院,听课备课,然后参加他们教研室的教研活动,选个章节给他们试讲。听课回来后,我们学校也准备上课,所以当时学校还是比较重视,不能只劳动,还是要上课。当时教师不够,学校就采取借的办法,比如数学老师从北京石油学院调不过来,就借一个;另外成都工学院也借了一个,调来了的付定文,赵正中,另外又分配来了黄森楠、刘汉宗、龙章树等。
还有一个就是采取专业课支援基础课的办法,因为基础课先上,专业课后上。比如《工程画》是基础课,先上完了才能上机械的课程,杨继盛老师就上过《工程画》;我也去辅导过数学,还有地质系陈根正老师,他是搞测量的,也去辅导数学。采取各种办法,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课。
“扁担箩筐学院”孕育了我校精神
下雨天上课的时候,教室后面放的全部是箩筐扁担,一大摞摞起来,扁担就放在箩里,他们戏称我们是“扁担箩筐学院”。
但要我说,通过锻炼的这批学生毕业后最受欢迎,他们能吃苦。石油部门当时是先干活后生活,我们的学生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培
养出来的,所以这个不在话下,到了现场不会叫苦。另外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比较老实,肯干活,到现场去都是老老实实地干活,领导安排什么任务就千方百计地去完成。
后来我们做教育调查,别人都欢迎我们学校的学生,所以在我们学校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很不错的。后来 58、59 级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到大庆,也没有一个人叫苦。
作为老师,要备好每堂课,批改作业是辛苦点,但不批改作业怎么知道学生的学习情况?如果发现有共性的错误,我就会想:是不是这个知识点没有讲到或者没有讲清楚,我就要再讲一下,通过这个我也发现自己的问题,这是我在教学过程中养成的习惯。
教书育人,我觉得关键是看行动。比如你要求学生好好学习,认真学习,如果老师备课、上课、批改作业都不认真,那学生还认真吗?要求学生做到的,老师得先做到才行啊!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你要求学生做认真,首先老师就要认真,言教身教是最重要的。
国家重点学科的申报之路
评审很严、很逗硬。重点学科是怎么评上的?那不光是写申报材料就行了,我们是提前几年就开始规划的。张绍槐院长谋划得很周密,不仅要求我们做了规划,还请了外面的专家来评审,有北京石油科技研究院院长秦同洛教授、成都理工大学的罗蛰谭教授,华中某单位的一位地质学科方面的院士等。张院长亲自主持,我作建设重点学科规划报告,专家依据重点学科的标准,如师资队伍、研究方向、科研成果、人才培养质量、获奖情况、国际交流等等逐项审核,是否达到要求、是否先进、有没有特色,还缺少什么、哪些地方需要加强等等。
规划经过反反复复地修改,几次评审后才定下来。学校才上报集团公司,集团公司审核通过了再往教育部报,教育部把材料发给评审专家背靠背打分评审,最后由教育部审定,不是那么简单的。
申报的具体工作及材料,张院长是亲自过问、逐字逐句地仔细讨论,不是一般的仔细,是非常仔细。我记忆犹新的是,杨坤鹏、罗平亚在深井泥浆处理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是重点学科的一个方向,我在申报材料中写的是“深井泥浆处理剂研究”,张院长亲自改为“钻井用新材料研制及应用”,把这个方向的档次一下就提上去了。
重点学科的成功申报,除了领导的组织和领导,我们老师也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没有计算机,做科研很艰苦。比如张院长的喷射钻井实验室,从实验室用房设计和仪器组装都是科研人员自己动手完成的;李士伦老师的相态研究,没有相态仪,就自己做,李士伦老师和孙良田老师把一块两百多斤重的不锈钢材料用自行车一个拉一个推送到外面汽修厂加工;任书泉老师的酸化压裂研究,为模拟酸化压裂的作用范围以及酸的浓度,自己设计并制造出了酸化压裂模拟仪;刘崇建老师为了开展固井研究,带领课题组老师在地质楼从地下室到楼,自己一手设计、制造、安装了模型井。当时的科研工作者很辛苦,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但最终研究出了很多科研成果。所以学校的重
点学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老师们长期奋战在科研教学第一线干出来的!
特别重要的是,在石油高校中,我们学校是最先取得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校。
油田口碑:有问题找“西南”
1987 年,我们申报博士点时,科技成果已经是一大批了,国家级的和部级的奖项很多,所以我们第一批被评为专家的是最多的。比如杨坤鹏、罗平亚老师他们搞的深井泥浆处理剂研究,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就有一些成果。深井泥浆与普通的泥浆不一样,它处在高温高压的环境里,在井下,每隔 33 米温度增加一度,超过五千米,你算一下多少度?
70 年代初,四川有个工程“7002”,七千米超深井,中央挂了号的。学校组织了一些教师长期在井队,有钻井的,是施太和去的;有泥浆的,就是杨坤鹏、罗平亚他们;有力学的,深井的钻杆是很重的,所以力学的老师去了。结果井队出现了一个问题,到 5000 多米固井下完套管的时候发生了井漏。当时用的泥浆我都看了的,从高温高压釜里拿出的泥浆像豆腐一样,根本流不动了,把现场的工程师脸都吓白了。油田的老总都上井了,像热锅上的蚂蚁,着急得很。
我们的老师、石油局的工程师们都在研讨处理方案,施太和把我也拉倒了现场。到了现场,我们重点研究泥浆怎么抗高温高压,我查阅了钻井的资料,根据井漏之前钻台上的压力是多少,下套管和循环泥浆之后的压力是多少,估算出了井漏时的压力是多少,得出的结论是因为泥浆上返时通道变窄、压力太大,将井憋漏了。在我们的参与下,现场重新配置泥浆把井给堵住了。最后固井的时候,我们建议他们排量不要太大,不然泥浆流速太大会导致井底压力变大,另外就是泥浆比重要合适,泥浆比重大了,井底回压也大,又要把井憋漏。这个事情为我们结合生产搞科研开了一个好头。
通过这个知道深井泥浆有什么问题,就知道怎么处理,形成我们独特的技术,按照我们这个方案处理,你的深井就可以打下去。杨坤鹏和黄汉仁通过这个事情编写了《泥浆工艺原理》,这是石油系统第一本系统阐述泥浆理论的著作。杨坤鹏是学化学的,黄汉仁是学钻井的,专业和基础相结合为我校的科研打开一条路:结合生产搞科研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出成果。
后来,在油田有这么一个说法:打超深井和泥浆的相关问题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我们的技术,有问题就找“西南”(西南石油学院)。
(文章刊登时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