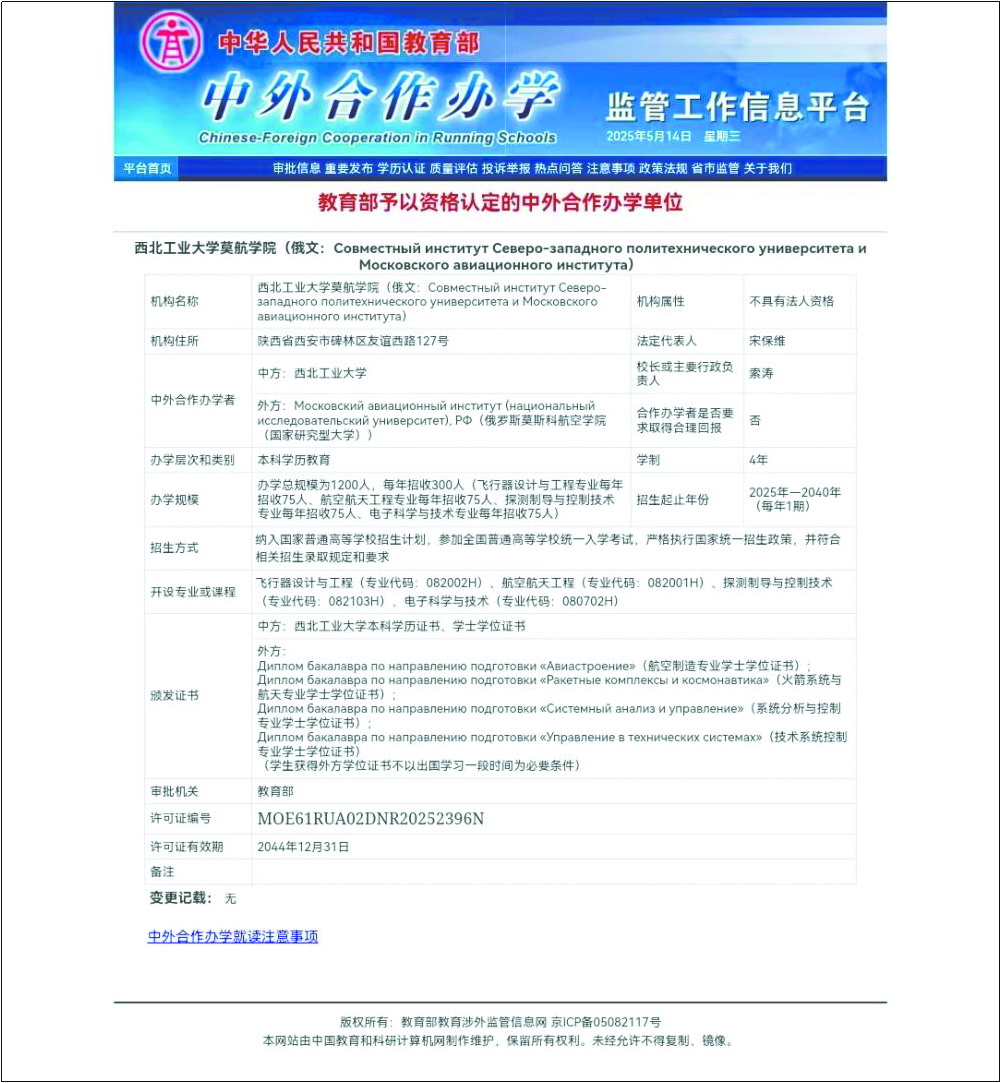我于1959年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系本科(现为上海交大口腔医学院)毕业,与8位同学被分配到安徽,我和罗永祥直接到安徽医学院(安医大前身)报到。其他同学分到地市级医院。当时有关领导给我们提示,希望你们到安医,参与口腔系筹建工作。然而报道后被分配到安医附院口腔科上班,第一印象在长江路门诊部二楼看到一块科室招牌“牙科”,连我们二人在内一共只有五位医师,二位技工,科主任李培智在北京进修口腔病理。我们上班后就从换科室牌子开始,把牙科改为口腔科,这也是当年由于学习苏联原因,口腔科比牙科包括范围更广。当时只有门诊,没有病房,正在这时附院外科主治医师柴仲培到西安进修整形、颌面外科,导师是有名的留苏口腔颌面外科专家——董淑芬教授。柴医师回来后要组建病房,开展工作,必须找助手,正好找到我们,因此,我们就参与组建整形口腔颌面外科病房,病房设在骨科病区10张床位,从此就走上整形颌面外科医疗之路,当时我们都住在长江路门诊部集体宿舍,病房在山上(当年没有绩溪路这个路名,原名叫东南岗,所以岗称山上)。我们就来回奔波,白天上完门诊晚上再到病房看望病人,参加手术后再到门诊上班,由于当时年轻也不觉得累,后来骑了一部旧脚踏车稍有改善,有一次在稻香楼附近为避免与对面车子相撞急刹车,跌倒在路边稻田里,爬起来并无大碍。后来搬到附院集体宿舍少一些来回奔波。
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饿肚子,工作照干,晚上还要搞政治学习、技术革新,搞到很晚第二天照常上班。除上班还要到学院给医学系专业同学上口腔医学课。
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病
房也撤销了哪还顾得上搞口腔系呢?柴仲培主任回到普外科,我们回到门诊部。文革后期响应毛主席6.26指示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被下放到铜陵农村当赤脚医生,当时还带了三位当地赤脚医师,如今赤脚医师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有的还在服务一线,至今仍有来往。
1972年应邀参加池州地区医院开诊,应张亚明院长(后任卫生厅副厅长)之邀调入该院口腔科工作,并且兼任池州卫校口腔教学工作,参编口腔教材。这一干就是十六七年,也获得副高职称。直到1987年,安医大、皖南医学院先后派人到池州地区人事部门商调,安医派出的是贾志书记、李亿松副主任,他们跟我说改革开放了,省教委同意开办口腔医学专业,目前人手不够,所以要求调你回安医。我当然愿意回安医,不是有句话叫“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于1988年秋天回到安医,被任命为口腔系副主任,实际上是常务副主任,李培智主任在附院口腔科上班,一般不来坐班,除非要开会研究事项,他才会来。
当年王生明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我们配合得很好,遗憾,由于年龄原因,再加上突然心脏病去世了。继任者是施秀英书记。
我虽然担任系副主任,后任系主任,但也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临床医师。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给学生上课时,全系大部分老师都来听课。当然也是接受群众的测评。
为口腔系建设尽了微簿之力。加强各教研室的建设,每个教师上课前都要备课,应有教案,并要在教研室内试讲,老教师提出评议,然后再上课。
请进来,派出去,曾邀请上二医口腔材料研测中心的张彩霞教授、孙皎教授来我系上口
腔材料课。我都在家庭里招待她们,以尽地主之谊。并挑选周健老师、张黎老师到外地进修德语,并安排张黎到上海九院进修儿童牙科,安排朱明英老师到附院口腔科进修正畸等。举办华东地区六省一市口腔医学教学研讨会。参会的有邱蔚六教授、浙医杨明达教授、福建陈树华教授以及江苏、江西、山东等同仁参会,会后承蒙潜山民营牙科诊所程维来医师接待到天柱山旅游。建立口腔系门诊部,大部分教研室的老师既是教师又是临床医师,没有门诊部就不能上临床。
近年在一次聚餐会上原副校长许占山同志还提到当年根据你的请求批给你两万元筹建口腔门诊部。利用当年学校服务公司几间商店旧址,加上豆腐坊旧址。筹建了口腔门诊部,当年有的同志就跟我说“你能搞起来一个口腔门诊部就是为口腔系立了一大功”。有了门诊部,医师都有了临床展示的机会而且有了收入,改善生活。学生也多了一个实习基地,并且建立了周一早会制度,便于互相沟通。这里特别要提到的就在这个小门诊部还接待了新西兰民间牙医代表团,除了会上交流,还参观了门诊部,互相交流了种植牙的经验。并在门诊部门前合影留念。
不断扩大实习基地,除省内附院口腔科、省立医院口腔科、合肥市口腔医院,并向外地发展,上海九院给予大力支持,并且开辟了海员医院、纺一、纺二医院及镇江市口腔医院、蚌医附院口腔科等。而且经常派老师去巡视,实习结束前派老师进行临床技能考核。
开展科研工作,当时我们在省内首先开展种植牙工作,并得到附院动物实验室协助,做了种植牙动物实验研究,并结合研究生课题发表有关论文。另外开展三叉神经痛、病
理学研究,发现三叉神经痛的神经分支有空泡变性的改变,这一发现与全国名校论述相同,取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0年即由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口腔药物成方手册》以后又参编《现代临床遗传学》、《口腔医学美学》等。当时条件所限,家住五工区工棚房,办公室仅有一台吊扇,每天只好利用下班后在办公室内写作,办公室白天有五个人同室办公,条件相当艰苦。
利用出差机会向兄弟院校学习,并协助采购教具——综合治疗台、仿真头颅、石膏模型等,增添实验室设备。
利用担任社会工作,如《中华口腔医学杂志》编委(第四、五两届)、《口腔材料杂志》、《现代口腔医学杂志》等诸多编委,学习先进经验,带回系里改进工作。先后担任安徽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顾问等,共同开展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工作。全力支持孙少宣教授开展开发口腔医学美学活动,并被选为安徽省口医学美学学会委员参与学会活动,参编第一本《口腔医学美学》专著。并被合肥市第一家医学美容医院聘为专家顾问团的成员。
司徒曼丽总结民间黄蜀葵的口腔粘膜病临床治疗作用,在我的任期内请校园李师傅帮忙在校园内种植黄蜀葵,将其花蕊晒干并请中医附院储希林药师加工成药膜,用于临床,取得很好的疗效。但一直未给予储希林药师相应的报酬,至今回忆起来仍感觉遗憾。
黄蜀葵的研究曾引起已故徐叔云校长、马传庚博导的重视,据说要开发成新药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及科研力量,故未能继续下去,留下一些遗憾。利用业余时间编写科普文章,向报刊、杂志投稿,退休后仍然坚持撰稿,并被《安徽老年报》评为“热心作者”。
相互协作,请附院口腔科负责人担任口腔系工作,我本人当年还被附院聘为口腔科主任,但有名无实,只有去开了两次会,查了两次病房而已。
多年耕耘,获得硕果,当年毕业生现在都是领军人物,如附院口腔科后军副主任、皖南医学院口腔系王云副主任、柴琳书记、蚌医口腔系主任张凯、省立医院口腔医学中心张志宏主任、朱祖武主任医师、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主任医师江宏兵、上海九院儿牙科主任博导江俊教授等。留校任教的毕业生都担当了重任,作出突出的奉献,就不一一列举了。
退休后一直担任教学督导组工作,深入课堂、认真听课,肯定青年教师的优点,婉转地指出青年教师的不足之处。
值得欣慰的是前年我与周健、何家才三人获得上海交大口腔医学院颁发的“震旦奖”。
虽然自己出了微薄之力,但还是靠党的领导,以及全体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古人云:温故而知新,我们一定要遵照党中央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要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向先进的医学院校学习,把我们的口腔医学教育事业更上一层楼。
1997年口腔医学院大楼正式落成,周健教授接任口腔医学系后升格为口腔医学院并任院长。自前年由何家才教授接任口腔医学院院长,除加强本院建设并且先后在市内筹建四个门诊部,扩大了服务范围,锻炼了队伍,新的院址更大正在筹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