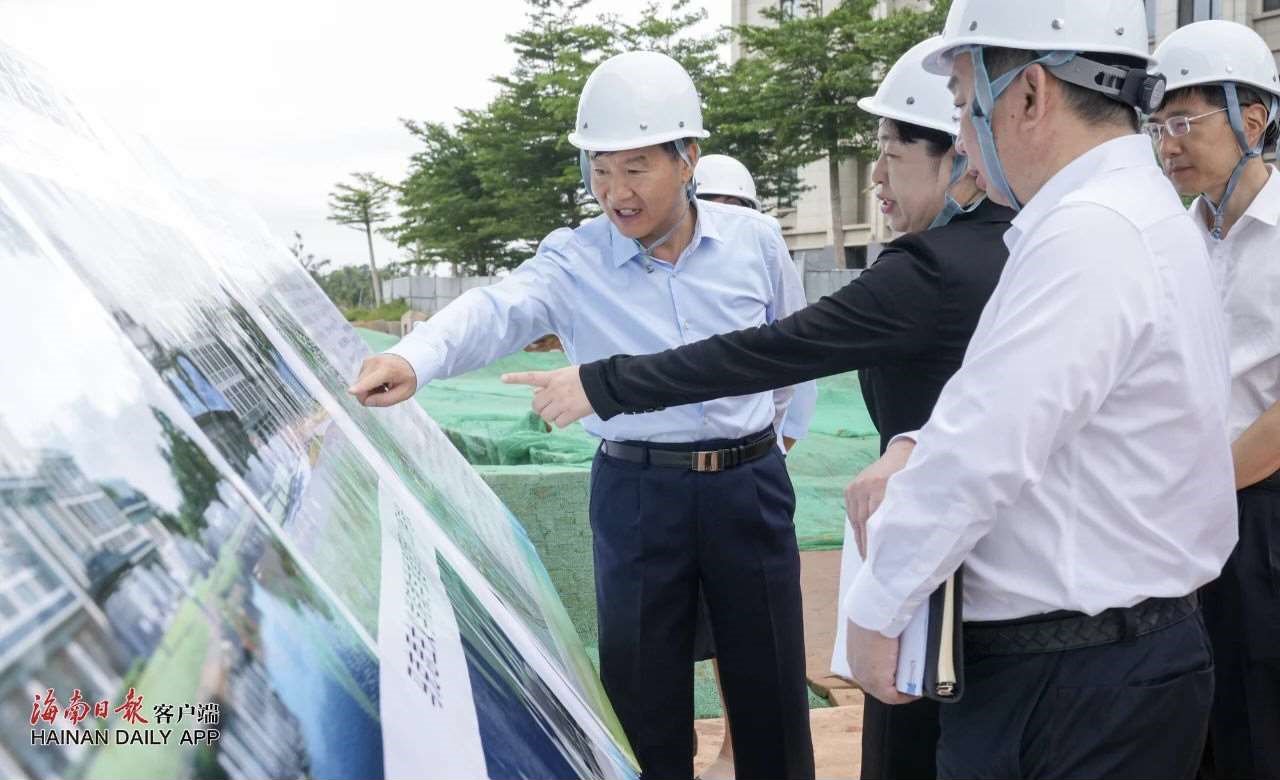姥姥家院子里的槐花树, 也是我童年故事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小时候, 对姥姥家最深的记忆, 就是院子里的那几株大树。在春夏之际, 榆钱、 桑葚、 香椿芽……都是我所喜爱的; 但最爱的, 莫过于那几棵老树上的槐花。
江南有桂花, 听说花开时节能够张扬地 “香飘十里” , 用桂花制成的桂花糖、 桂花糕是江南有名的小吃, 精致味美。可惜, 我不仅从未尝过, 更无缘一睹桂花 “芳容” , 只有想象。不过, 因柳永的一句 “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 而使金主完颜亮起 “投鞭渡江, 立马吴山之志” 的桂花, 想来也不差了。
在我印象中, 能与桂花相媲美的, 只有槐花。桂花我没有见过, 但既然能够 “香飘十里” , 香气想必很浓郁吧。槐花的香气虽并不浓郁, 甚至若有若无, 但总会萦绕在鼻尖,无论多远或者多久, 总会有一股淡淡的清香隐约可闻, 当想细心感受这香气时又倏尔消失, 并不强烈, 也不张扬, 总会缠绕在身畔心间, 像母亲的叮咛, 又像远方恋人的牵挂。
槐花的模样也甚为低调。淡淡的白色, 一串一串, 一簇一簇,隐于绿叶之间, 不像日本樱花火炬一样的耀目, 也不像柳絮一样惹人讨厌。 槐花总是低调地、 默默地开放着, 丝毫不理外人的赞美或忽略, 套用网络上的一句话: 只想安静地做着自己。 然而这些年有一种红色的槐花, 淡紫色的, 香气浓郁张扬, 听说还有毒, 完全是失去了槐花的本质, 这叫什么槐花呢?
槐花之所以能得到我的认可, 还有一个原因———可以吃!江南的桂花糕、 桂花糖, 精致甜腻, 糯米面软糯, 令人食指大动。 其精致的外形, 与其说是小吃, 不如说是艺术品, 像江南烟雨,像才子佳人, 像吴侬软语。
同样以花为主料的槐花糕, 却透着一种北方的粗豪。槐花糕很简单, 和好的面里倒入新鲜洗净的槐花, 揉均匀, 捏成空心的窝头形状, 上锅蒸就行了。 蒸出的槐花糕表面粗糙不平, 丝毫不如桂花糕如玉般温软的外表。 大小更是粗豪, 略小的都像拳头一般大,大些的一碗都装不下。如果说桂花糕是江南才子, 那北方的槐花糕就是江北武士, 豪爽实在。
还有一种槐花饼, 叫什么 “呱嗒” , 只能用这个奇葩的谐音来代替那没人会写的真名。 这个我很喜欢, 把槐花和面粉掺在一起,调成面糊, 捏一撇盐, 在平底锅里的油烧热后摊在上面, 一面凝固后, 再翻另一面。此时, 油香与花香不内敛地释放, 随着热气氤氲在空气中, 印象深刻。
槐花也是可以生吃的, 一串槐花, 冲洗干净, 捏着槐花的细茎放入口, 轻轻一拽, 只剩一条光秃秃的花枝, 槐花已尽数入口。咀嚼几下, 唇齿留香。
还有槐花蜜。每年春尽, 总有一个养蜂人带着几十箱蜜蜂和一只硕大的獒犬在这里暂住。在他的房子里还有几桶蜂蜜, 每当有人买,他总会认真地介绍这些都是什么时候采自哪里的蜂蜜。他最自豪的便是槐花蜜, 每年春天, 总会带着蜂箱开着卡车去几十公里外的大片槐林, 绝无半滴别样花蜜。他的槐花蜜, 一打开,就会有一种甜甜的槐花香弥漫扩散, 令人沉醉往返。
槐花是摇不下来的, 要用一根长铁钩拉下槐花所在的那一丛枝叶, 有时甚至折不下来, 空抖一地落叶。槐花也不好折, 要躲开树枝上的尖刺, 又要采尽槐花, 非是简单功夫。每次收拾完, 总有一大丛的带刺的枝叶无法处理, 只能用袋子包了, 扔进垃圾箱。
长大以后, 外出读书, 很少再见槐花, 事情多了也无暇去发现它, 偶尔在脑子里闪过, 便陡然地从内心深处涌起无限的伤感, 如烟的童年故事浮上心头, 惹得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下来。而悠悠逝去的往事如同漫漫冰冷黑夜里的灯光一盏, 让心头重又滋长出一点的温馨。
小时候, 自己永远都会跟在姥姥屁股后面, 吵着嚷着要吃槐花饼槐花糕, 姥姥总会骂我小馋猫, 但还是会给我做。 我看着姥姥做完的美食, 还不停地说着好话: “姥姥好厉害啊, 姥姥好厉害!”姥姥总会摸摸我的头, 说我是鬼丫头, 倒会哄人。 槐花饼刚做出来时烫得厉害, 姥姥就会给我吹吹, 有时候会拿扇子扇着, 嘴里不停地叨念着: “凉凉, 等等……” 槐花蜜冲水, 也让我无限喜爱, 小孩子, 总喜欢吃甜食。姥姥会拿两个大白碗, 放两大勺蜂蜜, 倒入凉开水, 总能让我喝个精光。
时光荏苒, 岁月流逝, 姥姥也已经老了。掠过心尖的风如同划过一片芳草地般拂过, 掀起海波样的清新气息, 情不自禁就露出曾经拥有过的孩儿般甜甜的微笑。我们都不曾忘记, 固然有时拥有沉入梦中的痴迷, 亦有梦醒时分含着酸涩泪滴去回味那份淡淡的苦楚。有时候想再尝尝槐花的滋味, 却总是错过花期, 无奈。人也老, 树也老, 姥姥说树上的槐花这两年不多了, 桑树的桑葚落得也快了……心里一酸, 在匆匆流年中, 我们又抓住了什么?
槐花里的记忆, 是永远回不去的昨天, 永远回不去的美好, 回不去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