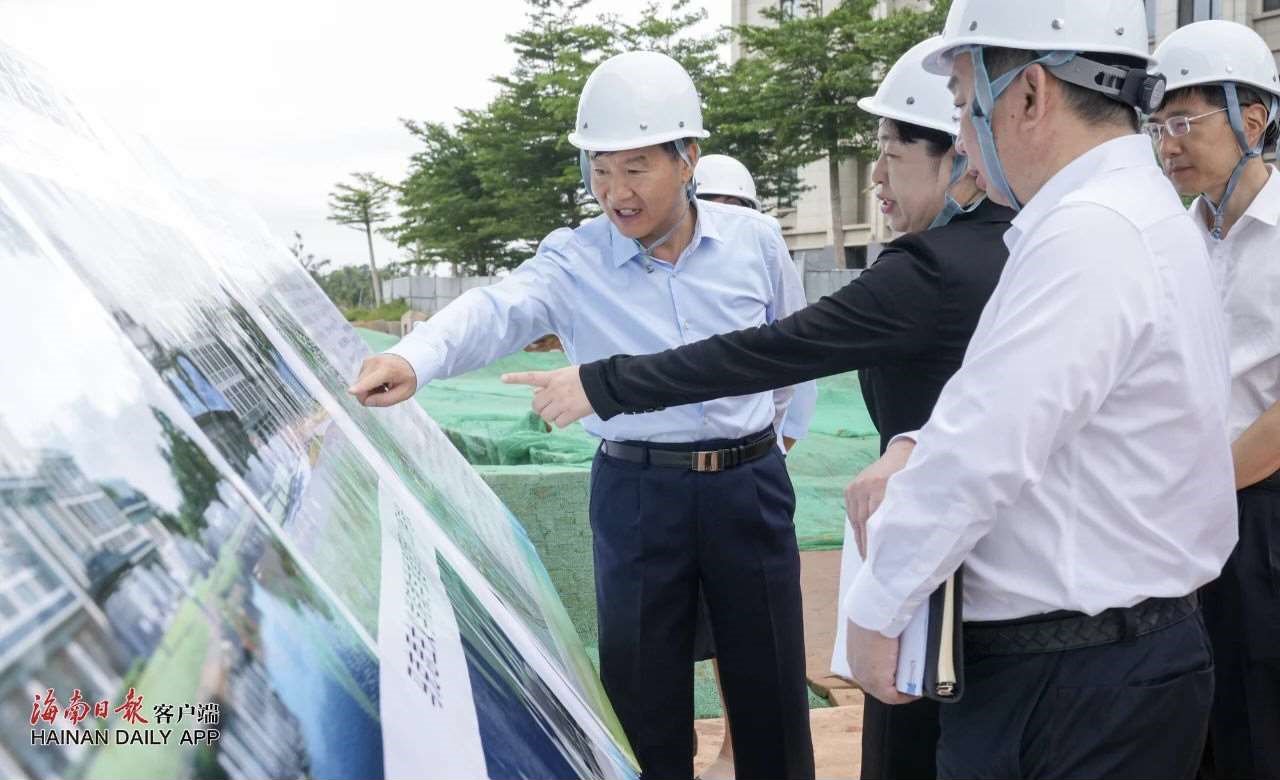“刘彦昌哭得两眼泪汪汪”、“王朝马汉一声吼”、“家住陕西韩城县”……
盛夏一趟西安行,走在布满法国梧桐的街道上,依然能感到拥挤的林荫间叶子筛下的细碎阴凉,可以听见路灯投射下细细的银亮声响。
有一种日月,叫做月是故乡明。而再次与西安的月相聚,恐怕又是短暂相聚后的长久别离。
十年前中秋,随父亲回部队探望,首长正带了一行人回陕北慰问文工团退休的老兵。是夜,灰厚的黄沙中四处张挂彩带,正赶上他们的戏班。
演员上场,一律背身掩面,女演员就碎步后移,水上飘一样,而男演员则摇动帽翎,一会双摇,一会单摇,一边上下飞闪,一边纹丝不动。待其猛一转身,怒眉一竖,高吼一声,声如炸雷豁啷啷从人们头顶碾过,凛凛之气越过台下观众轰然袭来,惹得脊背乍紧,发丝惊竖,全场一个冷颤……戏过一半方才平静,中场换角时,那演员在黑暗中瘫倚墙头,虽累到极致,扔伴着鼓点、和着曲调、翘着脚尖、捻着胡须悠然听戏。黑夜中有一滴纯净闪了光亮。
时光一流转,便悠悠。
想及此,他剧烈的咳嗽声打断了脑海中的轰鸣,当初他住院,我曾答应给他买一个烟盒般大小的收音机,他愈病重,愈是发堵,咳嗽声亦愈是刺耳。紧盯脏黑的墙壁裂了道缝,那缝隙似乎蔓延到屋的墙角,生怕他愈重的声响会让本不坚固的建筑瞬间坍塌。
惭愧蔓延。
再次见到,为他挑选了合适的收音机放入旅行包。他已病重了,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我将收音机调到秦腔的电台,轻轻放在枕边。他微微转过头,睁开凹陷的双眼,一行浊泪顺着眼角悄悄流出,沿着纵横交错的皱纹,艰难地滚落到病床上。他伸出嶙峋的双手,颤颤地向床头摸寻着什么:“花这个钱干什么,忘了跟你说,我已经有收音机了……”他的女儿帮他拿出来,真如烟盒般大小,缝隙里堆满了黑色的油垢。“这是他在21所(核电站研究所)捡破烂时捡来的,回来装上电池,拍一拍,还能响。”
午后鹅黄色的光线在玻璃上轻轻摇晃,清甜的微醺中,他的侧脸与耳边黑旧的收音机,格外纯净。
甜亦秦腔,苦亦秦腔,我想,秦腔之于他,正如色釉之于瓷土,油彩之于画布,墨韵之于宣纸般纯净,掺不得丝毫杂质的纯然。
他离开在深秋。家人承他遗言,只请了一个自戏班,丧事一切从简。远处放牛的老汉扯开嗓子放了一段信天游,一曲高歌响遏行云,一声入耳荡气回肠 。“彦章打马上北坡,新坟更比老坟多,人生一世莫错过,纵然一死怕什么……”瘦骨嶙峋的老牛拖着古老的木犁低头耕耘,天外仿佛传来他哼的戏曲,仿佛从天外传来,如闪电一般,俶尔逝去,繁星万点纷纷飘落。
残阳如血,军人向他行最后的军礼,我缓缓举起手,像是举觞敬酹一樽兰陵美酒,纯净地、洇入他长长的酣梦。
又是一年中秋,西安给我的印象或许是一番华清池的长恨歌,或许是正中轴的钟鼓楼,我看见了咿呀学语时就学的幼儿园,可是老师早已经离散;我看见了儿时嬉闹的伙伴,可是童趣也渐渐变淡;我听了一曲秦腔,想起了那老人的戏班……
生在西安,便一生认了第二故乡,而老人的戏曲长在黄土里,一词一句怕也是不小心触及了思念。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让我想起,盛夏的月圆。我站在高高的山梁湾子上,凝视远方暮霭沉沉的黄土高原,皓蓝的苍穹下,一轮朗月轻挂,梧桐缺处,分外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