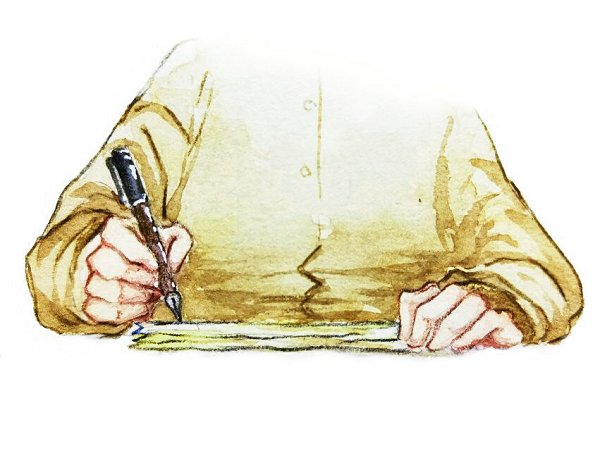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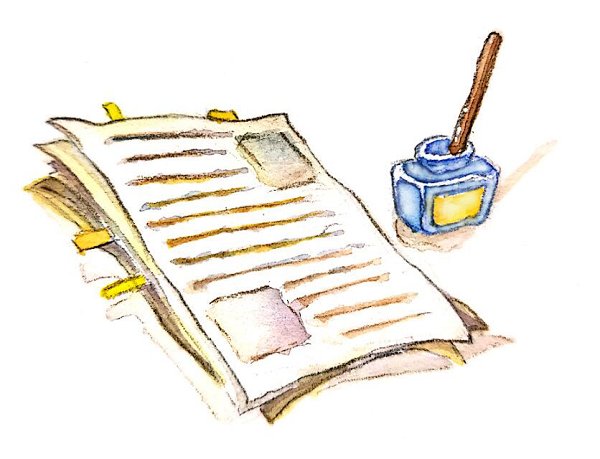
(图/张紫宁)
1992年,硕士毕业的周相录来到我校,至今已有26年。从昨日青葱年少,到如今硕果累累,周相录教授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始终保持着当年那般纯粹的心,守护着学术的一方净土。
周相录先生现为我校文学院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韩愈研究会理事、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理事,主要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唐诗研究、古典文献学等课程。26年来,他见证了文学院从没有硕士学位授权点到现今拥有多个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由硕士学位授权点到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转变。2004年,周教授接领导安排申报古代文学硕士点,凡事力求亲力亲为,其中不乏琐碎细事,但周教授尽职尽责,参与申报的每一个环节。2017年,周教授又全程参与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博士授权点的申报工作。
提及教书育人,周教授说:“大学阶段的学习不单单是教材知识的学习,更应是思维能力的提高,我们应该把学生培养成高素质、有思想、有一定学术研究能力的人,而不是一个只会技术的技工,只有这样,国家才会进步。”周教授认为现在很多中学老师缺乏辨别文献真伪与权威与否的能力,有些老师出试卷时直接从网上寻找材料,而有些材料经过多次转手,其中的内容“来路不明”,这样有错误信息的试卷会对学生产生不好的影响。他觉得,教师不仅要让学生学会分辨信息真伪,更要让学生明白从哪里“进货”可靠。虽然周教授常有一周二十多节课时的教学任务,但他也没有把研究工作搁置一旁,在2017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中,他的《白氏六贴事类集》项目成功获批。
由于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周教授不轻易相信事物的表象,并带着适度怀疑的眼光去看待周遭的事情,而他把这种习惯也带进了对类书《白氏六贴事类集》的整理中。周教授对《白氏六贴事类集》的整理工作主要是校勘。他用“给文献洗脸”的比喻为我们解释了这项工作:“我们要做的是把错误清理掉,还原文献问世时的本来面目,为后人的研究提供更准确的文本。”面对卷帙浩繁的类书,其整理的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当被问及如何去发现其中的问题时,周教授说,有些错误可以一眼看出来,有些则要认真对校多个版本,必须心细如发。在整理过程中,周教授曾怀疑某个字错了,但存世诸本均未发现不同,他在翻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终于发现了问题之所在,纠正了千年以来存在的错误。学术研究的过程虽然很辛苦,但解决问题收获的乐趣支撑着他在学术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周教授主要研究古典文献学与唐代文学。他说:“由于唐代文献基本都是手抄的,不易保存,存世文献比较少。而且,唐代文史研究得比较充分,处女地非常少,因此,很多研究唐代文学的人都把自己的研究后延了。”周教授明知研究唐代文学困难重重,但他依旧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在提及为何着重研究元稹时,他说自己对元稹的研究并不完全是因为兴趣,更出于一种求真的本能。他在翻看元稹的相关文献时,发现许多错误,认为自己有责任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他坦言自己也不会做得完美无缺,自己能做的就是将不完美接近完美。周教授说:“元稹同时代的人对元稹评价很高,为什么后来的人对元稹的评价越来越低?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需要去探索。”在周教授看来,元稹是一个被丑化、被误解的人,为了揭开历史的真相,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真实的元稹,从1999年开始,他就对元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申请过国家社科项目 《元稹其人及其创作的接受史研究》(2011年),并出版过《元稹年谱新编》、《元稹集校注》等著作,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元稹研究专家。
周教授在研究古代文学时,不仅仅研读与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献,也会阅读和涉猎大量历史、地理、思想史甚至是科技史等方面的书籍。“知识面宽一些,最大的好处就是思维不僵化。思维方式的影响是无形的,虽不直接,但作用很大。”他笑道,“我的优势在‘杂’,看书多,什么方面的书都看。”周教授的知识面不囿于文史,他对科学也颇感兴趣。读博士期间,他曾购买过一本《航空航天技术》,看得津津有味。小的时候,也曾花费很长时间看别人修理机器,琢磨每一个零件的作用。他说,好多东西总想着弄明白其中的道理。正是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心,支撑着他对古代文学、古代文献的深入探索,并乐此不疲。
26年过去了,周教授依旧将自己定位在书生位置,他不追求外在的功利,将自己置身于学问的帐篷内,一心只希望把自己喜欢的学问做好。“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只是一个比较好奇的人,一个还算比较勤奋的人。”他将学术研究当成一场求真游戏,从对历史真相的探索中获得乐趣。周教授说: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他将沿着求真探索的道路继续无畏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