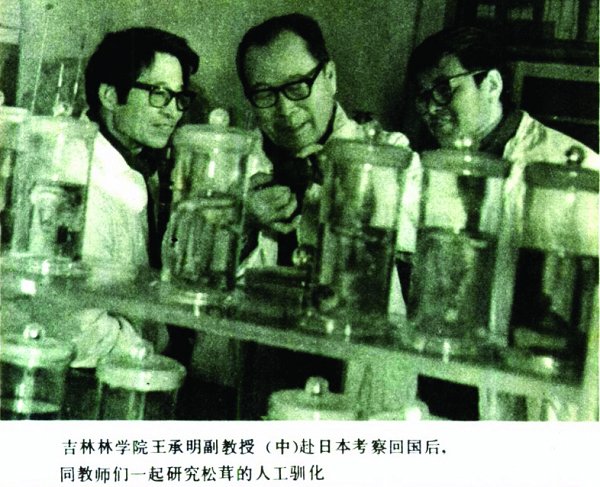
图片1980年代原吉林林学院王承明副教授赴日本考察回国后与同事一起研究松茸人工驯化
几十年人生的历程之中,对我人生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在大学读书这四年时光。我就读的这四年岁月,也正是高校“五四”以来高擎着的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迎风招展的日子。
如果不是国家包下了大学生的全部费用,以我家那时拮据的经济状况,即便我金榜题名,也是难以跨进大学之门的。如果是晚几年我才得以报考,出身又成为评判人的先决条件,以我家旧时沉冤的政治处境,即便我名列前茅,也是不可能被录取的。
百年不遇我逢辰。入学两年半正值院校调整,几个系被并于东北林学院(即今东北林业大学)。合并前我就读于吉林林学院林学系。记得开学后,王承明教授向新生介绍学院情况,讲过学院的光荣传统。话题转向景物环境———你们想要知道什么叫灵山秀水吗?请去看一看蜿蜒奔涌的松花江和龙潭山的“旱牢”“水劳”和南天门;你们想要知道什么叫历史沧桑吗?请去看一看北山的亭、台、楼、阁和旧时皇朝大臣们对小白山的朝拜。
作为学院学子,无论来自何方,都要受到这片沃土的濡染,永葆湖光塔影的情怀。忘不了美丽校园的春晓,环江晨跑,一棵杨柳一株桃,绿嫩红娇。忘不了学院庭深,静坐独吟,一架藤萝一片荫,祛暑清神。忘不了“两阁”风劲,漫步秋林,一层落叶一坡金,学富青春。忘不了“临江轩”敞,夜读寒窗,一帘冷月一席霜,心暖书香……
地利离不开天时与人和。我之眷恋湖光塔影,缘于它叠印着那个时代、那些人的亲切身影。好多画面恍如仙境,时常浮现于我甜甜的梦中。其间,每一想起便觉温暖而又伤感的,莫过于西庭桃红花下巧遇王承明教授了。
那是入学后的新春伊始,我从教室出来,索性被庭院前的一树繁花吸引住了。从未见过西庭桃红竟有如此肥硕者,满枝满树,如火如荼,怒放着茂密的花朵,妖媚端庄,婀娜多姿。我久立伫望,不忍离去。突然,不远处王承明教授和一位印尼华人走过来。教授向我介绍说,这位记者要拍几张我和学生在一起的照片。于是,我和他并肩朝校门走去。记者在前面倒退着边走边拍摄,教授告诉我,她那相机可以连续拍照……亲切如父兄,随和如友朋。
王承明教授对学生自称“兄弟”的口头禅,见于他给王战教授自称“矛尘兄”信的影印件,这是我到他家去拜望时才知道的。使我们过从密切起来的纽带,是他教授的森林植物学课程。摁了门铃进到先生的屋里,还是如十多年前那样小而暗,想想先生这样蜚声学术界的知名学者,还住在这样狭小简陋的房间,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但先生从来未因为此事而说过半点怨言。先生将我引到熟悉已久的旧沙发上坐下,便拉起家常来,几句话后便将话题转向他所教的森林植物学上。他说,森林植物学首先要掌握森林植物的形态特征和生态环境,从而为学习分类知识打下坚实基础。他又说,除森林植物学之外,还有森林学、树木学、森林植物病理学、测树学、森林气象学、森林生态学、森林土壤学、森林变迁及地植物学、森林昆虫学、森林狩猎学、森林鸟兽学……38门课程都和森林有关。那真是灵山秀水无所不及。花草树木应有尽有,林林总总,纷繁驳杂,“仙山”野趣尽收眼底,空谷狭峰美不胜收!
你们要如同吮吸母亲乳汁那样细细地品味着森林中的野味佳趣,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先生是一位治学极其严谨的学者,记得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从不乱说话,总要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一是一二是二,言必有据。先生每每向我们强调“打磨”于治学的重要性,先生上课,严谨而不刻板,可谓字字珠玑,条条锦绣,妙趣横生,里面不乏学问又兼有人生。其中所开设的“资料与方法”一课教我们如何收集积累拉丁文资料(植物学名以拉丁文命名)和研究资料的方法,对我们影响极大,每一堂课先生都要先检查我们的笔记,然后指导我们如何记录,对我们既是压力又是动力,为我们将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先生胸怀坦荡,为人极其正派,即使是那些文革期间整过他的人,先生也不记恨心上。先生总是对我们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他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他说,孔子甚至不无激动地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师生间的友谊与生活情趣。
余秋雨说:“人之为人,没有友谊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正因为它重要而又普及,势必出现不同的等级,不同的逻辑,不同的结果。其间,又隐伏着大量沼泽和陷阱。数千年来,人们因友谊而快乐,因友谊而安适,又因友谊而痛苦,因友谊而悔恨。天下小人伎俩,都会利用友谊;大量犯罪记录,都从错交朋友开始。因此,友谊,实在是人生的一大难题”。我们对于千古至谊,不抱奢望,却总是在寻找……
先生许多学生已经是享誉各界的商贾、学者、名人、官员,但他从不为此得意,更不会为自己的私事麻烦任何学生。先生与友人相见,总是在谈论学术人生,吟诗抒怀。“樱花红阳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当年曾在刊物上发表新诗,同友人叙旧:“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樱门岂偶然。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螯下酒话当年。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待得归华功满日,他年预卜买邻钱。”
在吉林林学院就读的两年多时间,先生定我和金学荣同学专攻“吉林省杨柳科植物(天然种)的调查研究”的论文命题。记得几次实习,先生独领我和小金同学去长白山调查。路线是从临江出发一直到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那是1962年4月初,我们从临江出发,乘汽车去长白,先生严肃地说:“上车后你们两个别害怕就行了!”我看了金学荣一眼,说:“您都不怕,我们怕啥?”他说:“那好,咱们走着瞧!”好家伙,汽车从临江城出发沿途经过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四道沟、老局所、老保甲、撂荒地、飞机岭、十三道沟一直抵达长白县。沿着盘山道,只有三米来宽,200米以下是滔滔鸭绿江,汽车几乎是在悬崖上行驶,人不敢往外望,惊险至极。尤其到“飞机岭”处,尽是胳膊肘子弯(即直角弯)令人毛骨悚然。看来不出先生所料,还是先生经验老道。
我们俩在先生带领下,从长白县城边缘的沿江山岭,经十三道沟、撂荒地、老保甲、老局所、四道沟、二道沟、头道沟一直采集到临江城。采集到的鲜标本,每天外业前尚须翻倒标本夹子,防止霉烂变质,一直翻倒到干燥为止,按树种重新制作模式标本存档。先生除了对杨柳科植物(天然种)的识别权威外,对长白山的各科属的野生经济植物亦是娴熟至极。我们有时随意在山涧抽取一棵小草让先生读取拉丁学名,先生随口吟出:“定名人Liliao(蓼);有时对每种植物学名竟能用日文译出,令人惊诧。
我们采集到的长白山杨柳科植物千余件模式标本存档,经先生鉴定命名并核对《吉林省野生经济植物志》、《关东植物志》(日)、《满洲植物论》(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吉林省杨柳种植物共鉴定出三属(杨属、柳属、钻天柳属)56种。(见模式标本图和分类检索表)论文发表于《吉林林业科技》(国际发行)1990年第1-3期。经省级鉴定认为填补了吉林省这一领域研究的一项空白,同年获东煤公司科技成果奖。
根据我的观察,先生的长寿之道就是“仁者寿”。一是生性豁达,胸襟开阔。先生研究成果卓著,但他却品操高洁,淡泊名利。他既不爱钱,也不与人争名。他热爱学术,热爱生活,总是将精神和注意力集中在科研上,读书绘图就是他的精神家园。脑中无杂念,心中无尘埃,他的心灵世界美好而纯净。二是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作为一个世纪学者,他的人生也必然会随时代的风云而沉浮,随世事的曲折而动荡,然而他却能以不变应万变。不变的是他的品德、操守和对学术的追求,其他如时局的变幻,人事的沧桑、他都能在睿智的守望和等待中转化成了有利的机遇。三是以诚待人,以善处人。虽然是一名学者,生生却平易近人,待人诚恳热情。这种大家气度,是先生健康的心理基础。在生理调摄上,并无刻意追求,他全身心地漫游于学术的境界里,心态平衡,生活有规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刻意养生,也不人为地伤身。
如今,斯人远去,音容宛在。凝视着先生的遗像,耳畔又一次回响起电视剧《南行记》中浑厚的男中音演唱的主题歌:“云一样的漂泊,梦一样的路,如今我只能在漫漫长夜,拨动心弦,侧耳倾听,听那琴声如诉。”
(作者曾就读于原吉林林学院,舒兰矿务局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