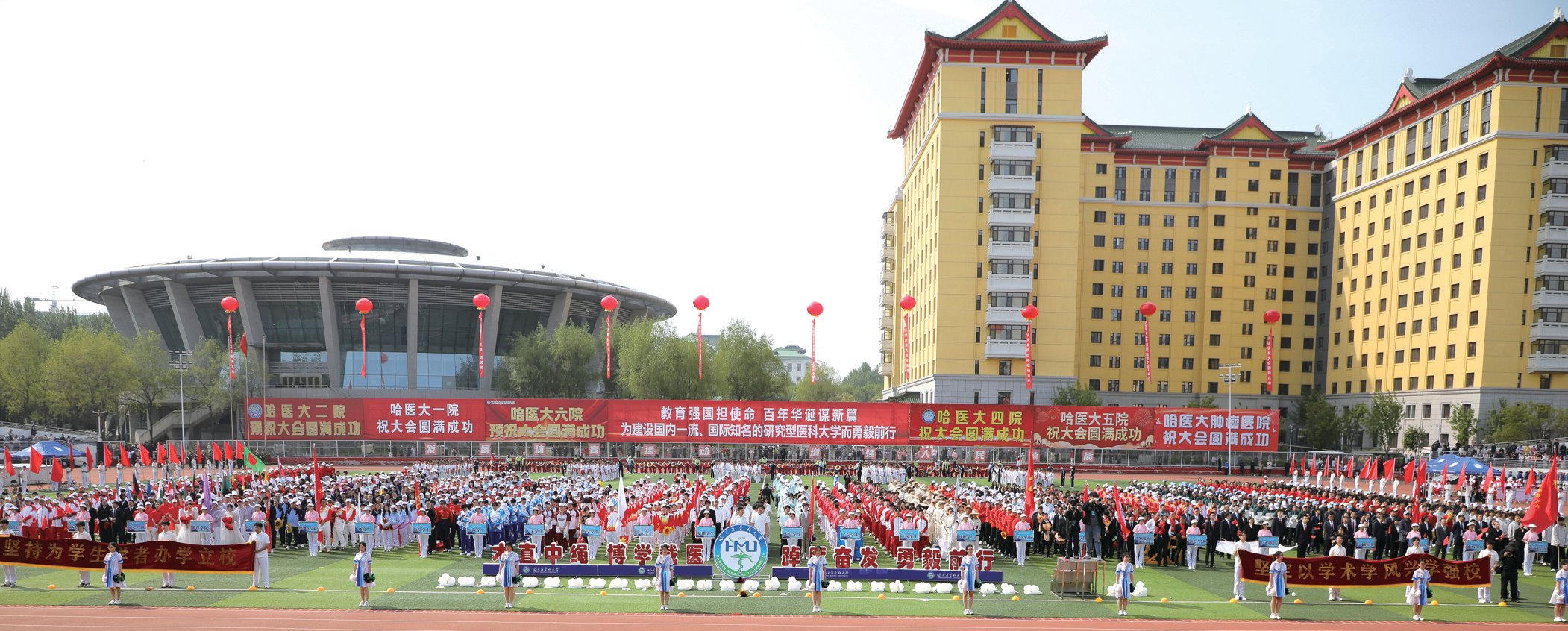一
不同于往年,今年的夏天来的格外早,也格外凉爽;早起时分土墙上都有氤氲的水汽,绿油油的草窠里,虫儿叫的正欢,望澜村的村民们个个都喜笑颜开,早早地备足了肥料和虫药,在自家的水井旁磨快了锄头,水珠顺锄把滚落,映着铁片闪亮的光泽;丘夏老人含着烟管,背着双手走在青石路上,“沙沙”的声响紧贴着布鞋,在环绕于村庄上空的“霍霍”磨锄声中显得并不突兀,弯曲的小路也恰似他的眉毛———挤作一团,“路也该修了……”老人一面想着,一面在两扇暗红色木门前停下了脚步,模糊的兽环在烟雾中清晰可见———村长温喜的家,木门承受了两声沉闷的叩击后便打开了,看清楚来人后,黑布下的圆脸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耳环也伴着嘴角的弧度摇晃着,“丘夏老哥,我正要去请你咧!”挽着臂膀,两团黑布进了堂屋;方才坐定,二人身旁便各多了一杯香茶,老人摘下烟管,轻轻地挡住了温喜递上的香烟,避开他询问的目光,只是盯着脚下的石板,不再说话,良久,彷佛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温喜,这天怕是要遭了旱!”村长一愣,点烟的手便僵在了半空,火苗闪了一下,灭了;笑声在堂屋中回响,温喜吐出一口烟雾,“丘夏老哥,今年夏天雨水足,小虫也少得多……”他抬头看了一眼老人,改口说道“不过今年夏天确实要比往年凉爽些,我也正奇怪呢,您老怎么看?”望澜村的第一神巫,他是不敢得罪。
“让乡亲们备足水,浇肥得用粪,用城里的肥土会结住,备好工具,准备挖水渠和蓄水池……”
“老哥,澜河上修的有水坝,平时蓄存的就有水,要是遭了旱咱放些水就够用了。”
“又是那个水坝!”老人猛地一拍扶手,烟管直指温喜的鼻孔,“当初我就不同意咱村修水坝,那可是澜河!你们敢在河神的头上动土!下游水都枯了,水坝旁边的土都塌成什么样了?这些情况我和村里面反映过多少次,哪次真正地解决了?温喜大村长!我看你到时候拿什么来防旱!”
温喜尴尬地笑了笑,转过头不去看老人喷火的双眼,水利方面的专业知识他是真的不懂,但修水坝是能给乡亲们带来好水的,是实实在在的好事,望澜村就指着这条澜河吃水,丘夏老人的心情他也能理解,望澜村敬河神,这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当初修水坝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勉强做好了老人家的思想工作,在乡亲们的用水问题上,他也只能扫了第一神巫的面子,老人心里憋着火,这他也知道,要不怎么会找茬似的在雨水充足的天嚷嚷着遭了旱?他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右手搓揉着烟卷,老人一瞅温喜不说话,揣了烟管便愤愤地走了出去,温喜从后面看去,老人像一棵树。
二
兴许是刚才起的有些猛了,老人的头有些发晕,摸着石板缓缓地坐下来,屁股传来的凉意让老人清醒了一些,呆呆地望着澜河粼粼的水面,河水卷着被揉碎的阳光缓缓浮动,像被剪碎了的火焰……
求雨仪式已经持续了三天。
这是四十年未有的大旱灾。
空气静得可怕,天上仍像是在下火,一片云、一点雨都没有,太阳炙烤着头皮,灼烧的感觉让人头脑发昏,村民们保持着下跪的姿势,眉毛埋进干燥的沙地里,粗糙的沙砾硌得人脸生疼,朝天的后背更是要开裂一般,但是没有人敢动,丘夏戴着面具,身着黑色斗篷,一条绿色的带子缠于腰间,对着火盆,疯了似地舞着,伴着手鼓变换着舞步,靴子震起的尘土洒进火盆,饱食黄纸的火焰却不曾衰减,像是要和天上的火焰一争高低似的,越烧越烈,丘夏的腰身也随着火焰扭动,蹬起的靴子搅不起一丝风;望着裸露的狰狞的河床,丘夏要绝望了,他能看见到处都有咧开的嘴角,在地上,在河床上,在天上,在耻笑他这个第一神巫,那道口子他心中越扯越大,就快要将他吞噬,他的黄脸上早就下了无数场暴雨,滴落进黄土里便不见了踪影;丘夏把手鼓扔进火盆,激起的烟灰四散开来,手鼓怪叫一声,“咯咯”的笑声便从无数个嘴角中涌出,拔出匕首划开掌心,血液漫过掌心的沟壑,顺着手指,绕着火盆洒了一圈,火盆烧的更旺了。最后,丘夏也跪了下来,合上干涩的眼球,抬起早已染红的手臂,举向天空,静默着。
人群静默着。
火盆仍在烧着。
日头仍在照着。
丘夏感觉有汗水滴落,又咸又苦,和血一样;天空似乎暗了些,但丘夏不敢抬头看。
浸润了血的斗篷在火光下泛着奇异的色彩,隐隐地有焦臭的味道从胸前散发出来,丘夏抬起身子,把匕首抵近喉咙,刀锋并不冰凉,还有些发烫。
丘夏感觉有血滴在鼻尖,他不敢睁眼看。
丘夏感觉有血落在身上,他不敢睁眼看。
丘夏感觉有血砸在头顶,他不敢睁眼看。
手鼓在火盆中爆裂,白色的刀子划过天空,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火盆哑了火,人群疯狂了,在水中打着滚,捧起雨水往嘴里灌,和着泥沙,和着丘夏的血,黄黑的色带在泥中舞动,天上的火赢了,天上的水赢了。
丘夏有些累,一头栽进了水坑。
雨下了三天。
三
水龙喷涌而出,巨大的轰鸣声将丘夏从回忆中拉回,巨大的水雾顺着澜河飞下,水流嘶吼着,将阳光拍碎,摔在两岸的沙地上,白色的水沫一会儿聚成团,一会儿又被冲散,无数匹白马在云朵中翻腾,鸣声萧萧,白色的鬃毛汇成流动的丝绸,裹挟着澜河往下游去了,看着河水,老人想起火焰。
澜河开闸!
轰鸣声中似乎有人在低语,仔细听时,是广播在坝顶上费力呐喊,温喜沙哑的嗓音在澜河上空回响,犹如水雾中的日光般时隐时现,“根据气象局气象预报……应对可能的中旱……主要集中在……已经得到许可……开放闸门……下游村民做好……”断断续续的信号淹没于激荡的水流中,温喜后来说了什么,老人没有听见。
河岸边,老人戴着面具,长过胡须的流苏左右飘摇,一袭黑色斗篷,向着奔涌呼啸的河水,尽情地舞着,靴底伴着鼓点踢踏着尘土,火盆的火焰随着影子摇摆,在厚厚的烟灰中变得扭曲,肢体正以着不可思议的角度扭转,白马在身后奔腾,扯碎的丝绸不时地被扬起抛下,在流动的白色火焰之中消失不见。
水坝就是河神。
老人朝着水坝跪了下来,眉毛埋进松软的泥土,口中默念着祷词;双臂扬起,掌心向着天空,老人像一棵树,举起黑色的枝桠,蜿蜒的血管穿过铜色的皮肤,宛如古树斑驳的纹路;浑浊的泪水漫过脸上的沟壑,滴落进沙地,融入高歌的水花,飞向看不见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