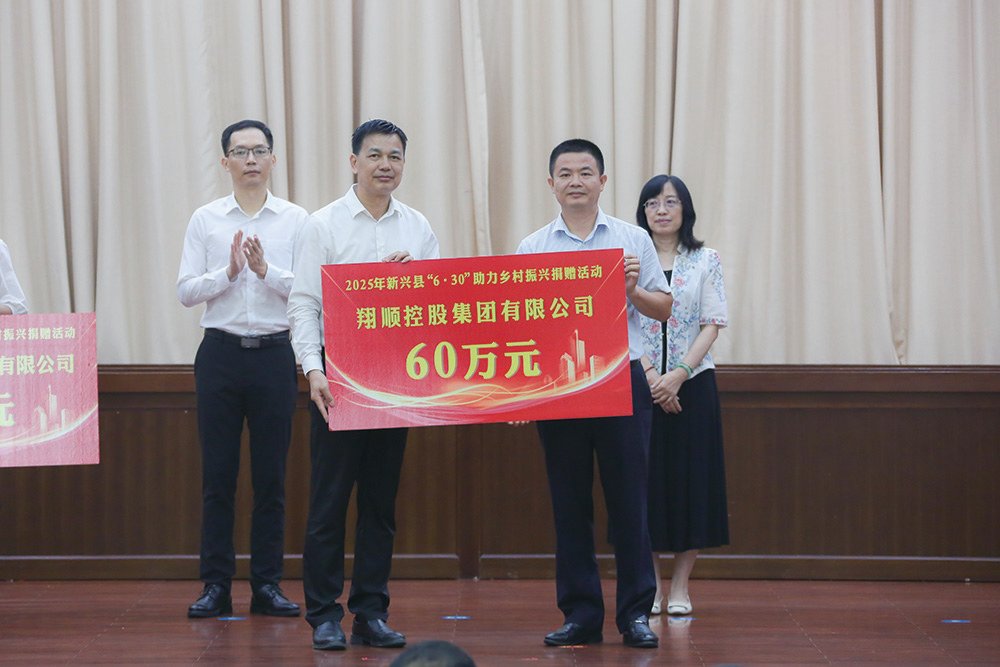走过那些岁月的老头儿们
姥爷八十岁做寿,请来一百多位当年的老战友老首长。于是,一群老头儿欢聚一堂。四川话、山东话、东北话、河南话不绝于耳。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历史性”的聚会。
一大群人颤颤巍巍、十几桌人白发苍苍。妈说,只几位部队大院的邻居她能认出来,那时候,她还没现在的我大。站在酒店门口,这接待是没法做了。须得老头儿才认得老头儿!好几次都是一双双布满皱纹的大手颤颤地来拉住我们面前的老人,把他领到安排好的位置上去,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老头儿们相见,格外地亲,大老远的就伸出手,然而又要很久才能紧紧地握住。有两位还欢呼着拥抱在一起,甚至要孩子似的脚不离地地雀跃一番。主持在讲台前致辞的时候,他们很认真地听着,时不时热烈地鼓掌,还响应老首长的号召,在一声口令下集体地、缓缓地起立,行了一个庄严的、沧桑的军礼。说话的时候,不管是威严还是和蔼的人,都用亮晶晶的眼深深地注视,高兴极了就洪亮地笑,这股子精气神,让人难猜年龄。
好率性的老头儿们。
他们的老太太有的还专门很正式地戴上一串珍珠项链,郑重地化了妆,穿上自己认为最好的衣服。老头儿们的打扮就显得普通了,T恤、布鞋、运动鞋,正式一点儿的也只是半旧的皮鞋西裤,或者自认为很郑重地在T恤外面套一件西服上衣———在这个暴晒到三十多度的大热天里。他们已经年迈,吃得很少很清淡,海参甲鱼们没怎么动,长寿面倒是剩得不多。妈说,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多都节俭成了习惯。这让我想起姥爷自己,他非常惋惜剩下的菜,总会抱怨我们打包带走的次数太少了。
这是认真的、可敬的老头儿们。
我一直很好奇的一点是,这些走过解放战争、三年困难等等极度困乏时代的军旅生活的人,为什么此后的一生都打上了朴素的烙印,即使面对越来越富余的物质变迁、日渐丰厚的国家供养?换作是我,我会不会想当然地穷及余生,以今之富余,补曾经之不足呢?然而姥爷姥姥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不在日常所需上“抠门”,他们也许会毫不犹豫地买好的数码相机、到海南福建东北旅游,但他们也会把散落在沙发上的芝麻一粒粒捡起来,把新买的拖鞋包好放起来,继续穿那双八几年的断了带的拖鞋,在一箱子烂掉的苹果里削下来能吃的部分……我想,这不仅仅是 “习惯”的问题,我相信这关于价值观、关于信仰。
生活在物质社会里,多元化价值观要求决定了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强求他人珍惜身边的物质资源,社会在号召我们追求成功的同时却对成功的价值观构建鲜有提及,并且对成功的定义有失公允:似乎成功就意味着金钱丰收、物质占有。比较身边已经工作的同龄人,有多少还在拿着自己不多的工资仰视奢侈的易耗品呢?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不知道他们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老人。
时间过午,老头儿们极简单地告别,坐上各地的车回去了,作息规律的他们还要午睡。
大概,这是不太一样的一代人,这是一群在我们身边的、每天都能见到的一代人。他们身上有着一些东西需要我们去发现、去进行“抢救性地继承”。
这些老人,让我想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