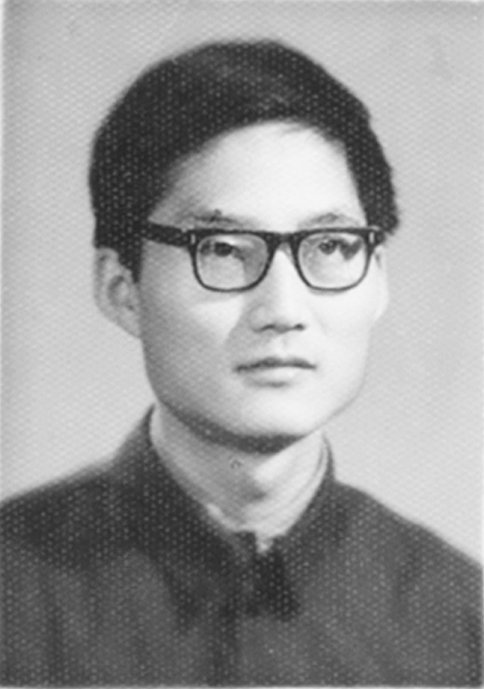
可以肯定地说,对于30年前参加过高考的人,那都是一段足以刻骨铭心的记忆。
从当时所具备的自身条件来看,我参加高考纯属偶然。1966年2月我和父亲所在的研究所一起由北京来到西安,当时我上小学5年级。不过我很快发现,这里5年级学的和北京4年级的教学内容完全一样。正当我准备跳到更高一年级求学的时候,所谓的“五·一六”通知把整个学校全搅乱了:高音喇叭取代了啷啷书声,“红宝书”取代了教材,温良恭俭成了腐朽没落的代名词,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接着而来的,是“停课闹革命”,是“革命的大串连”,是“消灭五分加绵羊,培养革命造反派”的教育改革…….对于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面对这一切,又新鲜,又惊讶,又惶恐,当然也有点着急:时间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而自己的学业还停留在小学五年级。当然,这期间也有特别的收获。一是糊里糊涂地从小学进入了中学,二是糊里糊涂地从中学进入到工厂。参加工作时我只有16岁多一点,当时的一个细节就让我至今难忘:履历表上有“学历”一栏,我左思右想不知道该怎么填,于是跑回学校去问老师。老师倒是胸有成竹,十分干脆地告诉我:“初中,但是没毕业”。
我参加高考也有着某些必然。这么说完全是出于那段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初次参加工作,肯定对什么都觉得新鲜,少不了会向周边的人们问这问那,而且问得最多的一定是自己心目中最有威望的人。一次,厂里的一位技术员十分认真地对我说:你的学习精神不错,最好能上大学。从那时起,我开始做梦,在梦中把自己和大学联系在了一起。那个年代,上大学不用考试,主要是由组织推荐,于是我向组织提交了上学申请,但是石沉大海了。1973年,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当年的大学可以通过推荐和考试两个渠道录取。兴奋的我觉得机会来了,再一次向组织递交了申请,并眼睁睁地期盼着考试。结果,当年涌现出了一位“白卷先生”将我的大学梦彻底打碎了。当我一遍遍听着电台上介绍“白卷先生”的壮举对中国教育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时,我发誓,决不再申请上这样的大学,并决心要通过自学和这样的大学较量一下。
对一个有工作压力的人来说,自学谈何容易。但是对一个被激怒了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从那以后,我成了全厂唯一一个每天背着书包上班的人,一个再没有节假日的人。在那个年代,一边上班一边读书是件非常熬人的事情,考验的不仅仅是人的智力,还包括人的体力和毅力;一边上班一边学习是件让绝大多数人不能容忍的事情,听到的不是鼓励,而是冷嘲热讽,风言风语。但是我始终没有退缩,咬牙坚持,终于用了五年的时间自学完了初、高中的全部课程。当1977年深秋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竟然哭了,就像一个受了很多委屈的孩子突然听到了母亲的呼唤。
我是1979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的是自己喜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从工厂到大学,从工人到大学生,巨大的变化使我对大学里的一切都感到特别新鲜。
首先是同学之间的年龄相差特别大。当时的大学生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应届的高中生只占极少数。十几岁的高中生和已到中年的社会学员同坐一个教室,除了给辨别谁是老师,谁是学生造成了困难,那两代人同读一本书的场面更着实有些滑稽。
其次是同学们的朴实。当时还没有校服之说,可同学们的实际着装却像约定好了似的,男生几乎全是四个口袋的中山装,女生几乎全是翻领的列宁装。而且颜色也大体集中在青、灰、黑三种。记的新生报到后的第一次集合,站队时我低头看了一下大家的脚,发现全年级一百多人中只有我一个人穿的是皮鞋。
当然,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还是大学里的老师。时至今日,他们在课堂上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霍松林先生那横贯古今的渊博,高海夫先生那平静语气中蕴含着的深刻,畅广元先生那激昂气势中时时流露出的睿智与胆识,马家骏先生那将教学内容烂熟于心后所产生的超然境界,尤西林先生那侃侃而谈中显示出来的思辨力量……
最初,这些老师在我的眼里犹如一个个身怀绝技的厨师,能把每堂课内容处理得有滋有味,像美味佳肴一样吸引着学生们的胃口。因此,每次上他们的课,我心里都会有一个从期盼到满足,从满足再到期盼的过程。后来,我把他们看成是蕴藏丰富的大山,除了外表郁郁葱葱,内里的涵养也十分丰富。他们是那样平易,平易得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走向他们;他们又是那样深邃,深邃得使人一眼望不到头。再到后来,我把他们看成是天上的星星,尽管距离遥远,但是有一种灵光会时时在你身边闪烁,失败的时候可以给你鼓舞,成功的时候可以给你鞭策,迷茫的时候可以给你指引,消极的时候可以给你力量……
在不知不觉中,我从他们身上学会了读书,学会了思考,也学会了做人,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生中的又一次质变。
记得有位作家说过: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关键的时刻就那么几步。的确,当30年的岁月弹指而过,回首往事,又怎么能不为自己当年迈出的那关键性的几步而暗自庆幸呢。假如没有当年那段如醉如痴的自学,我就没有勇气参加高考;假如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我也不可能遇到那么多学高身正的老师;假如没有这些师长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我也根本不可能使自己的人生轨迹沿着圣人们当年所设计的道路前行,走出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生命曲线,并在这一过程中成就了事业,体验了成功,悟到了人生真谛,而且,至今仍然能够在自己设计的人生舞台上无怨无悔地奋勇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