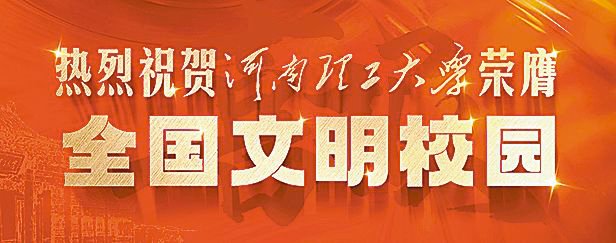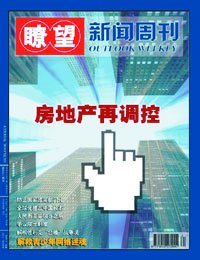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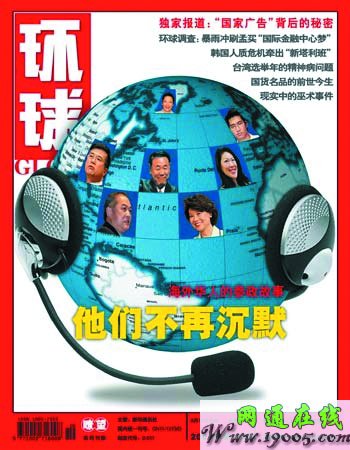
极地问题研究引起众多媒体关注
自今年8月以来,南北两极的新闻就不再只是探险或奇遇,而是充满了火药味的吵闹与纷争。加拿大、俄罗斯相继在北极举行了大规模军演,美国、俄罗斯、加拿大、丹麦、瑞典等国先后向北极派出了科考队,俄罗斯人甚至将一面国旗插在了北冰洋的海底。英国则于最近提出,将要求获得南极大片海床的所有权……而一时间,我国极地问题研究专家、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郭培清副教授的名字与“极地之争”和“中国的极地政策”等字眼联系得更紧密了。在一个暖意洋洋的冬日的午后,记者来到郭培清的办公室,就极地问题研究以及该领域目前在国内外的态势等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您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极地问题研究的?当时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研究的态势如何?
现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状况如何,您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
郭:大约始于2000年吧,在做博士论文查阅资料时,我看到美国国家安全文件中有关于南极的系列政策,当时有些好奇,觉得美国政府把国家安全的视野拓展得够宽的,竟然远涉南极!一查国内研究现状,发现尚未有人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国外的研究也不是很多,于是萌动了尝试的想法,在进行其他研究时,开始留心国内外的研究状况,遇到相关资料就收集起来。
当时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基础研究,这些对我的研究的开启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一直对这些学者充满敬意,比如原北大法律系的邹克渊老师,就是我一直想拜访的学者。
现在虽然南北极因为国际争端热起来了,但学术研究有其内在规律,必须有积累和 “发酵”的过程,研究热潮总得有一段时间才能出现。不过,学术研究的强大动力往往来源于现实需要。我个人估计,今年的极地争端会让极地政治与法律的研究迅速蹿升,极地问题研究的高潮就要到来。实际上,这在2007/2008国际极地年执行的项目就能看出来,在研的所有228个项目中,其中人文社科类约有62个,比例高达27%之多,这在前三次极地年是没有的,说明各国已经认识到极地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极地问题研究涉及的领域极其宽广,我涉猎的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跟国外许多学者相比,自己差得很远!越是深入下去,越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非常希望更多的极地问题研究爱好者加盟,壮大我国、也壮大我校的极地问题研究队伍。
记:您的专业方向是国际政治,这个方向有很多领域,其中不乏一些很热门的方向,您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极地问题研究这个在当时看来比较“冷”的方向?
郭:近年来国际政治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有许多人投入到国际政治的研究中来。在这以前,我曾经搞过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以色列外交政策、美国海洋战略、印度海洋战略等方面的研究,其中在以色列的外交政策研究方面也有一点自己的见解,但考虑到既然进了海大,就应该体现研究的海洋特色。
我曾经涉足的领域中,除了以色列外交的研究国内比较薄弱以外,其他的都聚集了一大批研究精英。如何树立起自己的研究特色,并把自己的研究方向与学校的海洋特色结合起来,这是我一直捉摸的问题。我想,除了要满足海洋特色以外,这个未来方向还必须与国家的战略需要结合起来。只有把自己的事业或者命运与国家的需要“捆绑”在一起,顺应学术研究为国家发展服务的基本方向,这样的研究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极地问题研究恰巧满足了这些条件,于是自己就选择了这个方向。
记:在您从事极地问题研究的多年里,有没有遇上让你懊恼甚至痛惜不已的事情,面对这些负面情形,您是怎样从中调整和恢复过来的?
有没有让您感到欢欣鼓舞的事情,是什么?
郭:极地问题研究为什么长期受到冷落?内在逻辑说明,如果一门学科发展滞后,肯定有其客观上的合理性,要么是因为资料缺乏,要么是大多研究者认为继续搞下去没有前途,所以才会从者寥寥无几。时至今日,有很多学科早已发展成熟,而且大都群英荟萃,留下的学科处女地已经很少了。极地问题研究之所以滞后,自然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资料缺乏就是困难之一,尤其缺乏原始文献,有时为了找到某个文件,不得不多次托朋友从国外帮助查询。资料的匮乏,确实消磨着我的兴趣和耐心,自己一度想转到其他方向上,比如以色列外交政策方面,这个领域国内搞得也不成熟,自己已经开始入门了。发表了几篇文章后,相关刊物的编辑也看好我的研究取向,好几次建议我继续做下去。可是从极地问题领域退下来自己心又不甘。于是说服自己坚持下去,相信这个交叉学科的春天迟早会到来的。
说到高兴的事情,当然一是自己希望的资料搜集到了,这种感觉太好了!所以平时和朋友聊天时,总喜欢说,如果有一天能有机会到《南极条约》的保存国———美国和南极条约秘书处的设置国———阿根廷走一趟就好了,到时候我就来个“超级”大搜集,以解我多年的干渴!到时候我要把所有的《南极条约》体系的文件、《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所有报告和会议纪要、北极的法律文件、各国的相关文件全都复印下来,建一个完备的资料库,凭借丰富的材料写出权威的文章来!
另一种高兴是自己提出了一些观点,往往一开始心里很没底,发表出来或者说出去后自己想,就等着批评如潮吧!可是等了很长时间后没有动静,既高兴———可能自己的观点站住了,又有失落感———只有切磋才能有长进。
记:到目前为止,您在该领域的创新有哪些?
郭:简单说,有这么几点吧。
在初步研究的基础上,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极地问题既是科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之说,这是一家国外媒体这么评价的。
其次,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的解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应该高度重视公约对外大陆架划界 (也就是超过200海里的大陆架)中“2500公尺等深线说”的潜在隐患。在国内现有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论述中,普遍认可“200海里说”和“350海里说”,认为大陆架最远只能延伸到350海里处,而对于“或不应超过连接2500公尺深度各点的2500公尺等深线100海里”的规定没有给与足够重视。实际上,这条包含“或”字的含混规定为国际争端埋下巨大隐患。重视“2500公尺等深线”的观点第一次提出后,说实话,我当时心里很虚,总觉得是不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别人都认为外大陆架最远可划到基线外350海里处,自己提出的2500公尺等深线之说正确吗?毕竟自己是个后来者。思考再三,还是坚持下来。我个人认为,打算吞并北极海底的国家就是冲着这一条而来。倘若按照2500公尺等深线扩张下去,那么北极海底将只剩下南森海盆和加拿大海盆的盆底留给全世界,其余的全部被环北极国家瓜分,连马卡罗夫海盆都剩不下。因为北冰洋是世界上最浅的大洋,平均深度只有1300米。俄罗斯高度关注的罗蒙诺索夫海岭沿东经140度线通过北极,中部山脊距洋面1000米左右,其最高峰距洋面只有900米。
再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极地争夺的“科学导向”问题,即极地暴力扩张时代已告结束,因为参与极地争夺的都是大国和强国,战争恐怖产生的平衡使得极地争端只能通过国际法途径解决,而国际法的支点将最终落实到科技贡献上,只有拥有科学数据,才能对于其他国家的权利主张提出反主张,并维护自身的权利。因此,科学考察和科学研究是我国极地话语权的重要依据。
第四,分析了南极科学研究与南极旅游对南极环境消极影响的比例关系,认为科学研究给南极环境带来的消极影响远远超过旅游,只不过是因其巨大合理性掩盖了对它的消极影响罢了,提倡合理、适度开展南极旅游,建立中国在“南极旅游业者国际协会”中的话语权,因为你没有开展旅游,你就没有资格参加这个高规格的国际旅游组织,当然也就没有你的声音。
当然,这些虽说是创新,但仍需要时间检验,尤其欢迎其他研究者进行交流。
记:在国内,从事极地研究的人着实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讲,您是一名极地上孤独的行者,艰难地行走在极地研究领域。那您是怎样克服这种“孤独”的?
郭:每个学科总得有人搞,况且是客观现实需要。很盼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这个领域的研究,互相探讨,共同努力,使这一学科的研究取得更大进展。
我个人认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对资源需求的无止境,与极地丰富的资源之间迟早会发生碰撞。上世纪在能源危机的70—80年代,国际社会曾经为了南极资源的分配打过嘴仗,最终达成协议冻结南极法律现状,但这种冻结本身就寓意着冲突。有冲突就需要有研究,与其晚研究不如早动手,总不能等到《南极条约议定书》规定的资源冻结最后期限,即2041年之前我国才开始研究吧。任何学科的发展总都需要时间酝酿。
记:无论是南极还是北极,都与海洋有着天然的联系。而您执教的中国海洋大学又是国内最高的海洋学府,在海洋方面,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走在了国内其他高校的前列。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对您的研究有没有帮助?您是如何把它们转化为自己研究的助推剂的?
郭:您说得很有道理,极地问题研究属于交叉学科。不但需要历史、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也需要了解大气科学、海洋物理、海洋地质等学科中与极地有关的基本知识,否则,研究就缺乏深度,甚至可能出知识性错误,所以遇到相关的内容,就常常请教我校理工科的老师。由于这些知识是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让我自己看书捉摸,周期会很长,于是就向我校一些曾去过极地或者从事相关研究的老师请教,比如赵进平老师、林霄沛老师等等,特别要感谢赵进平老师,因为他南北极都去过,是我的重点请教对象。老师们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把深奥的极地自然科学知识讲给我听,使我对极地科学有一些初步的了解。所以说,海大的海洋学科基础为我的研究提供的支持是其他研究者难以获取的,这里我由衷地庆幸自己工作在咱们学校这种良好的海洋学科氛围之中。没有这些支持,我的研究开展起来会无比艰难。
咱们学校其他文科院系中从事海洋研究的老师也是我经常拜访的。比如,在进行极地文化的初步研究时,我请教了文学院的修斌老师和曲金良老师,把曲老师关于海洋文化的文章都看了一遍,这些帮助让我受益匪浅。
记:国内外多家很有影响的媒体,对您进行过专访,或者是刊发过您的署名文章,这也是社会对您在该领域地位和资历的一种认可。您自己怎样看待这个事情?
郭:我只是能算是一个初入门者和侥幸者,越研究下去,自卑感和焦虑感就越强,发现还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去研究。极地问题研究离不开海大的海洋学科氛围,这点微不足道的进步首先归功于咱们学校。在这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的时代,单靠一人之力是干不成事的,有许多人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是我难忘的,只有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研究搞好,这是自己的本份,也是对学校和帮助过我的老师的回报!
记:请谈谈极地问题研究这个领域的走势和您的打算。
郭:今年8月份因为俄罗斯北极海底插旗,引发了极地争夺战,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人们发现,单纯关注极地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已经过于狭隘,各国肯定都会下大力气进行极地问题研究,这些都值得我国学者关注。我国在这一轮极地问题研究的高潮中不能落后,必须努力赶上;否则,将严重影响我国在极地事务中的话语权。当前,我国出现了学术智慧与政治资源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对我校的极地问题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如何抓住这一机遇,迅速提升我校在极地问题研究领域的地位,牢牢占领研究高地,同时为国家的极地战略研究服务,是我们的义务!
极地问题研究对充实我校研究的海洋特色内涵,提升我校在国内外海洋学界的声望,大有帮助。
除了继续深入研究以外,今后,我个人认为应该努力关注两个建设———资料库建设和团队建设。关于团队建设,国家有关部门也提出了要求。盼望有一天能由我校主持召开极地问题研究的“武林大会”,出现澎湃如潮的研究局面!
记: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北极和南极的争端再起。请问这次“极地争夺战”的实质是什么?为什么俄英等国在这个时候掀起新一波极地争夺热潮?
郭:这次“极地争夺战”实质上是俄罗斯等国对冷战后现行国际秩序与国际机制(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挑战。俄罗斯敢于扛旗当头,不仅是冲着国际法盲点而来,还有其现实主义政治的考虑。北冰洋插横同战略轰炸机恢复远航、组建东方司令部等举动一起,都是俄罗斯 “展示肌肉”行动的一部分。此外,能源战略在俄国家整体战略中占据核心位置。除了内收(将能源经营权收归国家)以外,外扩也是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极海底的能源自然被纳入外扩的视野。
英国的南极“圈地”行动既是俄罗斯插旗的引爆效果,又是其上世纪初南极主权冲突的继续。
由俄英等国掀起的这一波极地争夺热潮,是全球变暖背景下气候重塑国际格局和能源秩序的典型事例。这场冲突正考验着现行国际机制(联合国和海洋法公约)的调节和适应能力。
记:北极和南极在国际法地位上有何不同?北极和南极问题分别适用于哪些国际法?
郭:在俄罗斯等国证明北极海底属本国大陆架自然延伸之前,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北极海底属于国际海底区域,属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而不能视为“无主土地”。而1959年的《南极条约》冻结了南极的法律地位.但南极尚不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它是一个“另类”———既不属于哪个国家,也非全人类共同财产,管理权现在属“南极条约组织”。
北极地区目前的国际法很不完善,对于北冰洋权益如何划分尚无据可循。在北极地区目前唯一能够发挥规范作用的当属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但该《公约》不足以保证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大陆架以及公海利用等问题的有序解决,尤其对于超过200海里的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规定充满了争议。《公约》规定,“大陆架在海床上的外部界线的各定点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350海里,或不应超过连接2500公尺深度各点的2500公尺等深线100海里“。这条包含“或”字的含混规定就是惹起争端的“罪魁”。俄罗斯插旗之举,就是冲着国际法的盲点而来。
南极情况不同于北极。1959年的 《南极条约》冻结南极法律现状,并禁止提出新的领土要求。但当时国际社会的资源意识和权利意识非常单一和狭窄,在法律制定上考虑不足,留下诸多漏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后,将南极洲大陆外围直到南纬60之间的海域(俗称南大洋)置于非常尴尬的地位。根据《公约》,南大洋属于公海范围。但根据《南极条约》,南大洋属于南极条约体系的管辖范围,南极条约组织是排斥联合国介入的。问题在于《南极条约》本身对于适用范围的规定也充满歧义。条约提出的“冻结”领土主权要求的原则,没有考虑到附属于领土主权的诸如大陆架等方面的主权权利。
记:俄英等国在北极和南极问题上的举措是否违反了相关国际公约?这些国家的“占领”是否有效?
郭:从法律角度来看,俄罗斯插国旗没有任何意义。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起关键作用的是地质状况而不是插国旗的行动。这就是俄罗斯、丹麦、美国和加拿大都纷纷向北极派遣考察船进行海底勘探的原因。掌握的数据越精确,主动权就越大。
俄罗斯扩张大陆架的梦想面临着许多困难。要获得大陆架主权权利,必须获得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批准。申请国必须提供大陆架延伸处地质构成与200海里大陆架相同的证据。但是,北冰洋海底具体勘察资料获得难度之大,世人皆知。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说法,俄罗斯已为研究和开发北极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投入的资金数额已是天文数字,但北冰洋海底地形仍有许多地域模糊不清。俄罗斯申请通过的希望渺茫。
英国的南极“圈地”梦想也很难实现。英国声称依据《公约》伸张自己的南极权利,但其申请明显缺乏有效、有力的国际法支撑。随着南极条约体系的完善,《南极条约》涵盖的范围呈扩大趋势。《南极海豹养护公约》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都明确指出适用范围在南纬60°以南,甚至往北扩展到南极辐合带,表明南极条约体系已开始限制原先所谓的公海权利,发展自己有关南极海域的规定。照此理解,作为缔约国,英国根据《公约》提出的权利主张更加站不住脚。
记:目前的极地争夺对中国有何影响?
郭:极地系统是地球整体系统的一部分,它直接影响全球的大气环流、大洋环流和气候变异。因此,两极地区的自然过程及其变化深刻影响着我国的海洋、气候、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极地丰富的资源储备是人类本世纪下半叶和22世纪发展的重要资源保证,而我国人均资源极度匮乏,加之现行的海洋法公约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因此极地的未来对于我国影响重大,关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否享有发言权,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有所作为。
记:中国的极地政策是什么样的?面对目前的“极地争夺战”,中国应该注意些什么?
郭:邓小平1984年为中国南极考察的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至今仍是我国极地工作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
迄今为止,我国对极地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有限的经费维持着尚不全面的自然科学研究,而对极地除科学以外的其他信息了解甚少。极地问题不单单是自然科学问题,更是一个人文社会问题,涉及政治、法律、外交等诸元素。不管哪个国家,如果缺乏对极地政治与法律等问题的研究,届时必然被排斥在极地决策事务之外,处于被动地位。
我认为,中国应抛弃“局外中立论”,距极地遥远不是我们漠不关心的理由,今天中国正从地区性大国走向世界性大国,两极发生的事情关涉中国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应防范部分国家抛开中国,私下协商建立地区性多边条约体系,从而损害中国的极地利益。这一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已有俄罗斯学者在鼓吹建立“极地八国联盟”。
文/本报记者 金 松《参考消息》记者 谢开华摄影/伯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