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山东大学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推进“人文社科振兴计划”,弘扬“文史见长”传统,全面提升人文社科学术原创能力、思想引领能力、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与传播能力、国际学术影响力,创建知名学术品牌,培育“山大学派”。在奋力进行“双一流”建设,实现山东大学“由大到强”历史性转变的征程中,如何打造人文社科学术重镇和原创思想策源地,如何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发挥山大作用,是全体山大人关心、关注的问题。在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召开前,山东大学新闻网———山大视点网站采访了学校20位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家。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治学感悟,以及对学校人文社科发展的殷切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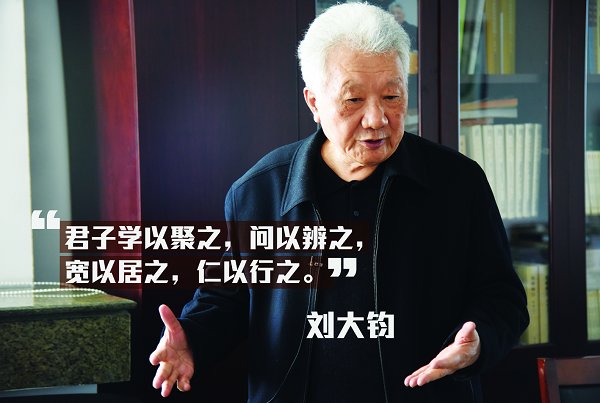
刘大钧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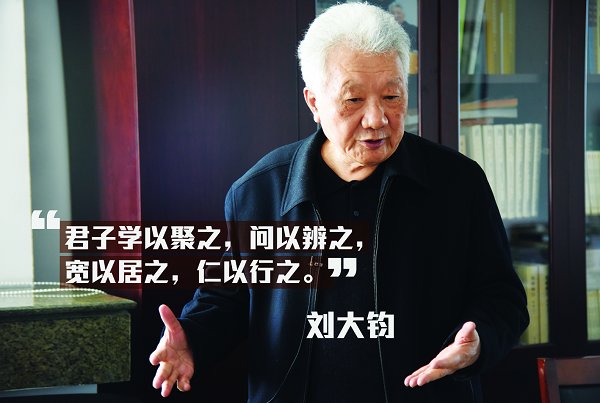
我的治学感悟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治学必须以德为首。《易经》中很重要的一句话,叫“进德修业、崇德广业”。什么是“德”?不显才为德。不要处处彰显自己,要谦和,有德的人不显美德。“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这是《易经》对于治学的一种见解和认识。
山东大学历史上在文史哲三个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里我想引用《中庸》上的一段话:“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是继承、发展前人的事业,将之发扬光大,这才是真正的“孝”。正如余纪元教授所说的,是实现前辈的期许、意志与梦想,是对传统的不断创新。希望我们时时、世世地对山大文史哲等传统优秀学科展现出前面所说的这种大善、大孝、大美。
我对学校今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寄予希望。随着近年来西方文化走向中国,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互相交流变得比过去几百年频繁得多、范围大得多;因此,中国的经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创造性发展。如何发展经学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展中国哲学中最鲜活、最有生命力的部分的问题。一些西方著名的学者,如荣格,也吸纳了中国的经学研究,来发展本学科的优势。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即经学研究今后也要进一步拓宽视野。今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以更广阔的境界和视野,来对待经学、子学以及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自得圆融的状态下,把中国哲学的“大道生生”加以扩展。要用《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角度和内涵,发扬光大我们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
山东大学历史上在文史哲三个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里我想引用《中庸》上的一段话:“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是继承、发展前人的事业,将之发扬光大,这才是真正的“孝”。正如余纪元教授所说的,是实现前辈的期许、意志与梦想,是对传统的不断创新。希望我们时时、世世地对山大文史哲等传统优秀学科展现出前面所说的这种大善、大孝、大美。
我对学校今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寄予希望。随着近年来西方文化走向中国,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互相交流变得比过去几百年频繁得多、范围大得多;因此,中国的经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创造性发展。如何发展经学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展中国哲学中最鲜活、最有生命力的部分的问题。一些西方著名的学者,如荣格,也吸纳了中国的经学研究,来发展本学科的优势。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即经学研究今后也要进一步拓宽视野。今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以更广阔的境界和视野,来对待经学、子学以及其他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自得圆融的状态下,把中国哲学的“大道生生”加以扩展。要用《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角度和内涵,发扬光大我们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

袁世硕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
我1953年毕业,在山大学习、教书、做研究,这三个方面,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之所以成长,我觉得得益于一边学习、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这是一个最佳途径。我学习了老一辈老师的治学精神——实事求是,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传统的训诂学、考据学的方法,这些使我能够有志学、有路子、有遵循。另一方面,我受到原来的老校长的启发,重视学点哲学,学点理论,这对我研讨一些问题起到很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如果说我这一生写了一些文章,在我们学科有所创获,那还得力于在这两个方面有很好的学习。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有什么成就,只是想解决我的专业里发生、存在的问题。由于我提出的一些新见解,做出了一些成就,国外同行的专业期刊也都做过一些介绍,但这绝不是我的初衷。
我们学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文史见长,在全国高校当中,是公认的在文史两个专业方面走在学术前沿的。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研究走在学科的前端,做出了一系列成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二是我们的学生质量好。当时在各个专业,都有全国有名的教授始终坚持给学生上课,因此我们的课程比较扎实,学生的专业基础比较好,在工作上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给我们学校赢得了光荣,赢得了声誉。今后学校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争取再度辉煌:一是在科研上要有新的成就,在专业研究上有所创新,有所突进;二是学生的培养质量要超越全国其他学校的水平,让他们在工作上有所成就,为学校争光。

曾繁仁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
我的治学感悟是,把治学看成是人生价值的一种寄托或者提升,使人生更有意义和价值。我快八十岁了,在这样的年纪,还能做点有意义的学问,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我希望山大的文科秉持一个基本理念——“固本创新”,就是把原来的“本钱”巩固下来,然后再创新。我们的本钱是“文史见长”,中文学科在学科评估时是A类学科,我们有四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这一点“家当”要保持好,要在此基础上创新。学校重视文科发展,要数数“家底”,先把这些基本的保住,然后再开拓新的领域,我相信山大人文学科经过努力是可以振兴的。
教师是很崇高、很令人骄傲的职业,我认为对教师这个职业应该有敬畏心。我的目标是做一个各方面合格的老师,上好每一节课,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情。

路遥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
我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不只局限于历史学,是结合历史社会学来做研究的,这个非常重要。整个历史学科最多是与政治学结合来做研究。义和团运动研究难度很大,可以说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没有一个学者能够单独写成一本义和团史。义和团运动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能够列入世界大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义和团运动是怎么回事,怎么开始的?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当时国家把任务交给山东大学,以山东大学为主解决这个问题。当时义和团运动的相关材料是空白的,我们从1960年开始着手做。怎么做?从田野调查做起。山东大学整个历史系,从老教授到年轻教授统统下去做调查。1960年、1962年、1965年三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给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步我们做成功了,材料很多,已经出版了。我从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感悟是在研究中与历史社会学的结合。关于义和团运动,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对此评价很高,山东大学能够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牢牢地把握住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们山东大学研究义和团运动是一面旗帜,下了很大的功夫。十年一次的义和团运动国际学术讨论会,一共举办了五次,都是在山东大学举行的。
山东大学有一些特有的名片,今后应该考虑由学校组织力量促进其发展。义和团运动研究整整40年来都是山东大学的名片,现在只要想了解义和团研究,就要到山东大学来。山东大学还引进了德国的大学教授狄德满,是学校人文社科一级教授,编著了70多万字的《义和团大辞典》。义和团研究工作要继续增加力量,希望学校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文章千古事,甘为一布衣。我退休之后,希望学科后继有人,继续发展。

温儒敏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
我做的是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这些年做得比较多的是现当代文学,最近十多年又比较关注基础教育,所以我研究的范围宽一点、广一点。最早是做鲁迅、做文学史的研究,后来研究范围拓展开一些。文学与社会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这个学科,要解决一些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所以我希望这个学科的年轻人、年轻学者,要找准自己的学术发展方向,要找有意义、有价值的方向,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持之以恒地围绕这个方向不断地做。如果长期围绕有意思的、对社会有价值的题目,始终如一地坚持做下去,一定能取得比较大的成绩。就怕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项目搞了很多,最后一无所获,这是我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做现当代文学不能只关心我们学科本身,涉及面应当拓展一点。比如说我本身是做文学史的,这几年我到山大以后和研究室的人一起做文学生活研究。并不是说我是打井式的,一辈子就研究这一点,当然这也很好,也是必要的,也要有人这样做,但同时也应该有人做出去,做出去的意思是关注社会所期盼的、所要求的一些更有学术价值、更有分量的题目。现当代文学跟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山大的现当代文学学科也要跟其他的学科有所整合,所选的题目不应是层层相映、轻车熟道的,而是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新,同时又贴近社会需求、社会关心的题目。这样的题目是很多的,关键是能不能静下来认真去做。山大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方面都有积累,利用好这些积累是有前景的。
做现当代文学不能只关心我们学科本身,涉及面应当拓展一点。比如说我本身是做文学史的,这几年我到山大以后和研究室的人一起做文学生活研究。并不是说我是打井式的,一辈子就研究这一点,当然这也很好,也是必要的,也要有人这样做,但同时也应该有人做出去,做出去的意思是关注社会所期盼的、所要求的一些更有学术价值、更有分量的题目。现当代文学跟每个中国人的生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山大的现当代文学学科也要跟其他的学科有所整合,所选的题目不应是层层相映、轻车熟道的,而是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新,同时又贴近社会需求、社会关心的题目。这样的题目是很多的,关键是能不能静下来认真去做。山大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方面都有积累,利用好这些积累是有前景的。

张蕴岭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
我是山东大学外语专业出身,研究生招考的时候我报了世界经济系,有一个想法就是研究国外,看他们是怎么发展的。实际上我毕业以后做的工作就是了解国外,助力推动中国的对外开放。因为工作需要,我要懂国家政策,除经济外还要懂政治,懂国际关系,这就需要不断学习,应该说学无止境也做无止境。我体会最深刻的是,要有国家情怀,世界眼光。国家情怀非常重要,要做成一件事必须下大功夫,要带着当时的定位来做研究。推动中国参与区域合作是出于两个考虑,一个是中国的利益,另一个是区域和解、和平与合作。我带着情怀来到山大,推动成立了东北亚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院。办好一个学院,办好一个实验型的新兴交叉学科,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做起来的,还需要长期的积累。中国的一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不能没有,不能不强。国际问题研究是从国别区域开始的。中国崛起后显示的作用是能够有能力解决东北亚问题,使这一地区走向和平、合作。
山东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学校要为科研提供科研环境,除了引进人才,更多地是要思考怎么培养人才,培养更多的面向未来的青年,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甄别人才,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要有志向,愿意做;二是要有能力。山东大学要实行更灵活的、真正利于学者和老师们发挥其创造性的制度。教学应该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相信将来能够创造更好的条件。
山东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学校要为科研提供科研环境,除了引进人才,更多地是要思考怎么培养人才,培养更多的面向未来的青年,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甄别人才,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要有志向,愿意做;二是要有能力。山东大学要实行更灵活的、真正利于学者和老师们发挥其创造性的制度。教学应该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相信将来能够创造更好的条件。

王学典 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我来到山东大学已经40年了。最近在和一些青年学者、学人接触时,我经常强调几点:第一点,治学得“占领一个山头”,讲好一门课。所谓“占领一个山头”,就是得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这个“一亩三分地”里,即使不能保持“称王称霸”,至少也得有相当的号召力;在某一个专业范围之内,学问得做得很精。所谓讲好一门课,就是这门课要讲得无可替代,我觉得这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同时又不能画地为牢,必须把自己的学术根据地放在全局中去观察。换句话说,必须切实做好宏观和微观的统一,把你的治学根据地放在一个宏观结构中去把握、观察,才不至于固步自封。这一点特别重要。目前很多人考虑问题只是从一个点出发,没有放在宏观视野下去把握,所以常常会出现问题。第三点,青年学者必须在功力和见识上取得一种平衡。光有功力或光有文献的功夫还不够,思想和文献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才能成为优秀的学者。任何观点都不是靠文献自动产生的,它是一个互动的结果,要有你的洞察力、观察力和概括力参与其中。能把文献提炼、概括成思想、概念,才能在思想界站住脚跟。
我个人是做学术史的。在做学术史的过程中,我常常把具体问题放在学术史的视野当中、背景之下来观察,包括对山东大学文科的发展。我感到,即将召开的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非常及时,不光是山东大学的人文社科,整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视野都面临结构性的转型问题。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们经历了三次学术研究范式的变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正经历着从以现代化为中心向以本土化、中国化为中心的学术转型,目前还处在转型的开端阶段。我个人感觉,未来三十年,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和主要走向,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讲话中提出来的,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现在开始,我们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要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山东大学地处孔孟之乡,我们更有责任,也应该有担当,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转型中走在前列。我对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希望山东大学以这次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为契机、为起点,走在全国前列,走在学术界的前列。
我个人是做学术史的。在做学术史的过程中,我常常把具体问题放在学术史的视野当中、背景之下来观察,包括对山东大学文科的发展。我感到,即将召开的山东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非常及时,不光是山东大学的人文社科,整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视野都面临结构性的转型问题。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们经历了三次学术研究范式的变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正经历着从以现代化为中心向以本土化、中国化为中心的学术转型,目前还处在转型的开端阶段。我个人感觉,未来三十年,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和主要走向,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讲话中提出来的,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现在开始,我们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要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山东大学地处孔孟之乡,我们更有责任,也应该有担当,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转型中走在前列。我对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希望山东大学以这次人文社科学术工作会议为契机、为起点,走在全国前列,走在学术界的前列。

郑杰文 “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首席专家、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个人要取得学术成绩,不光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个人拼搏,更离不开师友的帮助,离不开时代的造就。感谢我的硕士学位导师董治安先生、博士学位导师南京大学的周勋初先生等学术前辈的引导,他们教会我以文献整理为深度学术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治学方法。我照此治学方法依次进行了先秦儒家、墨家、纵横家典籍,以及谶纬文献的深度整理和综合研究工作,撰写的《中国墨学通史》获评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领衔编纂的《中国经学学术编年》获评“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我感到十分荣幸。感谢山大古典文献学同行的信任,让我作为学科学术带头人,与全校30余名同行一道,拿到了古典文献学科的省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感谢山东大学的信任,在2010年春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把5个重大委托项目之一的“《子海》整理与研究”委托给学校时,确定我作为该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让我与180多个国内同行一道,复制影印、整理出版了1118种子部成果。感谢国家相关部委的信任,让我担任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首席专家。我将与数百名国内外同行一道,用10年的时间,基本摸清中华古文献在全球的存藏情况和学术价值,对藏于境外而国内缺失的汉籍做再生性回归,并加以整理研究,以完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存藏,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引领世界文化发展。学术道路修远漫长,我将继续上下求索,与同行携手努力,为整理中华民族古文化典籍精华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术是学者的生命。一个学者,最看重的是学术发展平台,是学术成果获得认可。愿学校尽可能为老师们提供所需的学术支撑,尽可能为老师们提供公正又实事求是的评价标准,使老师们能够心情愉悦地为学校实现“双一流”目标贡献各自的聪明才智。
学术是学者的生命。一个学者,最看重的是学术发展平台,是学术成果获得认可。愿学校尽可能为老师们提供所需的学术支撑,尽可能为老师们提供公正又实事求是的评价标准,使老师们能够心情愉悦地为学校实现“双一流”目标贡献各自的聪明才智。

杜泽逊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搞学问首先得用功,功夫用在读书上。如果一开始就按需求去搜寻资料,那原书的精神不能领会,整个传统文化的精神不能领会,本学科的主旨就不能领会,就解决不了为什么治学的问题。搞学问的长远目标,是人类生活所需要的精神层面上的创造,是引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所以做学问要有方向感,要往高的地方、美的地方去引导,这是我们的目标。而个人出点成果那是为总目标作贡献的一个小方面。此外,做学问需要追求创新。创新的前提是掌握前人已有的辉煌成就,要对前人的成果怀有敬畏之心。创新必须得明确新和旧的界线,明确了这个界线,那你在创新领域的成果越多,贡献就越大,就越能获得同行的尊敬。所以既要追求真正的创新,还要追求创新的量。在创新和量之间,先要保证创新,如果不能多创新,就少创新,不能因为追求量而淡化创新,那样的话就事与愿违了。
我们山大以“文史见长”,很大的一个背景是文史哲不分家。我们承担国家清史项目,承担艺文志,搞清人著述总目,这些都是文史哲交叉的,里面也有科技史。所以,不分家对搞中国古典学来说是一个原生态。山大中文学科过去很领先,这是咱们的精神力量。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做到领先,过去领先过,现在可能不很领先,但是也很靠前,我们还可以更领先。大家都去争领先,我们国家才有希望,才有可能引领世界。文学院尤其要争领先,我想应该有这个信心。外界有一些对我们的评价,总体看好,认为是在提升,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也应该变成力量,多努力,争取让它慢慢提升,但是不能冒进、不能躁。搞学问要沉下心来,欲速则不达,过去叫十年磨一剑,搞学问同样要遵循这个规律。
我们山大以“文史见长”,很大的一个背景是文史哲不分家。我们承担国家清史项目,承担艺文志,搞清人著述总目,这些都是文史哲交叉的,里面也有科技史。所以,不分家对搞中国古典学来说是一个原生态。山大中文学科过去很领先,这是咱们的精神力量。就是说我们有能力做到领先,过去领先过,现在可能不很领先,但是也很靠前,我们还可以更领先。大家都去争领先,我们国家才有希望,才有可能引领世界。文学院尤其要争领先,我想应该有这个信心。外界有一些对我们的评价,总体看好,认为是在提升,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也应该变成力量,多努力,争取让它慢慢提升,但是不能冒进、不能躁。搞学问要沉下心来,欲速则不达,过去叫十年磨一剑,搞学问同样要遵循这个规律。

黄少安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做经济学研究,和现在的年轻老师相比,我最大的幸运是从来没有为了评职称或者是一些“头衔”写文章。当时觉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肯定需要很多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我在考研究生的时候就想着,个人的理想要和国家、社会的发展相一致。那时写文章,是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自己有很多看法、想法,不写出来憋得慌。总结一下就是,自己对经济科学研究有兴趣,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
做基础理论研究的时候,可以追求自己不同的观点;但是做应用、对策研究的时候,一定要高度慎重,否则有可能祸国殃民。我这样想,也是这么做的,也这样要求学生。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理论、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有他的地位,一定是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有所发现、有所解释、有所作为;但同时也有他的局限性,没有必要崇拜、盲从。要敢于创新,创新的前提是你要懂得一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理论都应该重视,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创新。经济学的发展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来推动的,历史上重大的经济学创新和重要的经济学家,都是现实的产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大有作为,特别是在中国大转型、大变革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现在缺乏的是怎么把本土化的问题和国际化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年轻学者一定要坚持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怎么发现、把握问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转化成科学中研究的问题。
做基础理论研究的时候,可以追求自己不同的观点;但是做应用、对策研究的时候,一定要高度慎重,否则有可能祸国殃民。我这样想,也是这么做的,也这样要求学生。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理论、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有他的地位,一定是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有所发现、有所解释、有所作为;但同时也有他的局限性,没有必要崇拜、盲从。要敢于创新,创新的前提是你要懂得一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学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理论都应该重视,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创新。经济学的发展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来推动的,历史上重大的经济学创新和重要的经济学家,都是现实的产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大有作为,特别是在中国大转型、大变革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现在缺乏的是怎么把本土化的问题和国际化的研究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年轻学者一定要坚持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怎么发现、把握问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转化成科学中研究的问题。
(文/谢婷婷 张丹丹 何元航 孙筱纯 李昆 李琴 田俊腾 摄/侯滢 张丹丹 谢婷婷 王彦力 刀彦月 孙筱纯 刘晨)







